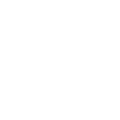母亲签下合同的当晚,家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沉默。
父亲看着那份印着“根悦会所”抬头的劳动合同,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这种地方被揩油是再正常不过了。他拍了拍母亲的肩膀,眼神里是浓得化不开的愧疚和一种无能为力的疲惫,转身走进了阳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心里堵得难受,知道那地方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新闻里那些关于合法化后的灰色地带报道像幽灵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可看着妈妈强装出的、带着一丝希望的笑容,所有质疑的话都卡在了喉咙里。我们心照不宣地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平静,仿佛不去捅破那层纸,噩梦就不会真正降临。
母亲的“夜班”开始了。
“根悦会所”内部比母亲想象的还要奢华靡丽。她被分配到一个名为“水云间”的包厢区域。起初的工作确实如合同所说,只是端送酒水果盘,更换烟灰缸。
但很快,真实的规则便浮出水面。
领班梅姐会私下“提点”:“雪峰,客人的手要是‘不小心’搭一下,你就当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让他们有点无伤大雅的‘亲切感’,你的小费才能厚起来。”
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秃顶的男人顶着一个肥猪脑袋,他第一次见到母亲,就露出眼前一亮的惊喜表情。这是母亲第一次遭遇咸猪手,她浑身僵硬。那只属于一个陌生中年男人的、带着烟味和汗湿的手,在她端着果盘时,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她的大奶上,很娴熟自然的大力抓捏起来,像一个面点师傅在漫不经心的揉他的两个面团。妈妈几乎要当场弹开,但梅姐警告的眼神和家里医院催款单的画面在脑中激烈交战。
她忍住了。她强迫自己脸上的肌肉挤出一个僵硬的、算不上是笑容的表情,将果盘放下,客人结束动作以后几乎是逃离似的离开那个包厢。
那天晚上结账时,梅姐塞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远超她基础工资的现金。
“拿着,王总给的,说你很懂事。”梅姐的语气带着一种“你终于开窍了”的意味,“你看,这差不多是你辛苦站几天电梯的工资。在这里,有时候你‘不动’,就是最好的服务。”
母亲捏着那个信封,感觉它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手心剧痛。那笔钱,可以支付爷爷好几天的特效药,可以缓解家里这个月的房贷压力。
母亲刘雪峰在“根悦会所”的日子,像在走一根逐渐绷紧的钢丝。那次默许客人的触碰以换取小费后,她给自己划下了一道新的、更靠后的底线——只到此为止,绝不再退。
她开始有意识地躲避那些过于“热情”的客人,宁愿少拿小费。直到一次,她服务的包厢,那个王总又来了,这次异常难缠,几次三番将她往沙发上拉,手也极其不规矩的想扒掉母亲的衣服。她仓皇逃出包厢,内心的屈辱和恐惧达到了顶点。
她在走廊上遇到平时还算说得上话的另一个服务员,小芸。看着母亲苍白的脸色,小芸把她拉到储物间。
“峰姐,还没想通呢?”小芸的语气带着麻木,“你以为我们在这里,真能只端盘子?”她随即告诉了残酷的真相——所谓的“性工作者从业执照”,会所根本不会为她们办理,就是为了降低成本、规避责任,让她们成为随时可以抛弃的“黑户”,并不意味着她们不需要从业。
母亲如遭雷击,连最后一丝关于“合法保护”的幻想也破灭了。她只想立刻逃离。
然而,就在这时,领班梅姐找了过来。她的脸上没有责备,反而带着一种“为你着想”的诚恳。
“雪峰啊,刚才王总那边有点不高兴了。”梅姐把她拉到更僻静的角落,声音压得很低,“我知道你一时放不开,姐是过来人,都懂。”
话锋一转,她开始了真正的工作:“但你要明白,咱们这里是服务行业,客人就是天。王总其实人很好哄的,你顺着他点,他手指缝里漏一点,就够你辛苦一个月的。”她观察着母亲的脸色,语气变得更加推心置腹,“姐跟你说,在这里,你想清清白白只端盘子,是不可能的。别的姐妹都……你总这么端着,客人觉得没趣,影响了生意,上面怪罪下来,姐也很难做啊。”
说着,梅姐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巧方正的东西,不容拒绝地塞进母亲手里。母亲低头一看,像被烫到一样——那是一盒避孕套。
“拿着,以备不时之需。”梅姐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关怀”,“女人嘛,总要懂得保护自己。路怎么走,当然看你自己是不是愿意。” 她特意强调了“自愿”,仿佛选择权真的在母亲手里。
紧接着,她的语气微妙地冷了下来:“但是雪峰,王总那边……你刚才确实惹他不高兴了。他要是以后不想再看见你,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在这里待下去了。让你来,是让你创造价值的,不是让你影响生意的,明白吗?”
这番话,像一套组合拳,彻底将母亲打懵了。
她的内心在疯狂挣扎,但所有的退路都已被堵死。梅姐的话、小芸的真相、医院的催款短信、家里的困境……所有画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她无法挣脱的巨网。
最终,那股支撑着她所有尊严和反抗的力气,像被抽空了一样,从她体内流逝殆尽。
她不再看梅姐,也没有扔掉那盒东西。她只是死死地攥着它,塑料包装的棱角几乎要嵌进她的掌心里。
她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轻声说:
“梅姐……我……我知道了。我……我去给王总道个歉。”
说完,她转过身,像一个被输入了指令的机器人,一步一步,僵硬地朝着那个她刚刚逃离的包厢走去。
她知道,当她再次推开那扇门时,走进去的,将不再是电梯员刘雪峰,而是“根悦会所”里,又一个明码标价的……商品。
这天夜晚,时针已经慢吞吞地爬过了十点。我心里像是有只小猫在轻轻抓挠,坐立难安。妈妈从来没有这么晚下班过,就算是加班,也该来个电话的。
这种莫名的恐慌感越来越强烈,最终战胜了“不要打扰妈妈工作”的念头。我拿起那只旧电话手表,它的塑料外壳已经被我摸得有些发烫。深吸一口气,我按下了妈妈的号码。
“嘟…嘟…”
听筒里的等待音显得格外漫长,每一声都敲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人接听时,电话突然通了。
“妈?”我迫不及待地开口,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你还在上班吗?什么时候回来呀?”
电话那头传来妈妈的声音,但和我平时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那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而且断断续续,中间夹杂着不自然的停顿和细微的、仿佛在极力压抑的抽气声。
“嗯…宝贝啊…”她的气息很不稳,“妈妈…还有点事…没忙完…”
就在这时,一阵奇怪的背景声音透过听筒钻进我的耳朵。“啪…啪…啪…”那是一种沉闷又有节奏的撞击声,不算特别响,但持续不断,让人心烦意乱。伴随着这声音的,还有一个男人低沉而粗重的喘息,像刚跑完步似的。这混合的声音让我心里莫名地发起毛来。
“妈,什么声音啊?你那边好吵。”我忍不住追问,手心开始冒汗,“你是不是在搬东西?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没…没什么…”妈妈的声音骤然绷紧了,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像是痛苦又像是极度难堪的颤抖,“妈妈在…在忙…你先自己睡…乖…”
她的话被一声短促的、被强行咽回去的呜咽打断。那“啪啪”声似乎变得更急促、更响了。
“妈?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摔倒了?你说话呀!”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种模糊的、巨大的恐惧感攫住了我。我虽然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本能告诉我,妈妈此刻绝不是在做什么正常的工作。
突然,一个陌生的、带着浓重鼻音和不屑的男声插了进来,语气轻佻得令人不适:“跟谁打电话呢,给老子赔礼道歉还敢分心?嗯?”
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凉了一下。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像是手机被粗暴地夺走。接着,那个男人的声音清晰地占据了听筒,他似乎在笑,声音里带着一种事后的、懒洋洋的满足感,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
“喂?小孩儿,找你妈?”
我完全僵住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好像嗤笑了一声,那种笑声让我非常非常不舒服,像被脏东西碰到了一样。“你妈正给我…‘服务’呢,没空理你。”他特意加重了“服务”两个字,语调怪异,让我联想到电视里那些不怀好意的反派。“你妈的嘴上功夫嘛…马马虎虎,应该没怎么练过……刚做这行,不太放的开…”他顿了顿,语气里的讽刺意味更浓了,“你小子,在家好好等着啊,等我这儿用完你妈了,我就让你妈回去…”
他的话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窒息般的恶心和困惑。我隐约感觉到,他话里每个字都好像在贬低妈妈,也好像在嘲笑我。为什么妈妈给他“服务”就不能接我电话?为什么他说“用完我妈”?到底是怎么用?一种巨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屈辱感和不安,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我死死地咬着嘴唇,仍旧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似乎觉得无趣,又像是终于炫耀完了他的胜利,最后含糊地、带着一丝不耐烦地说了句:“行了,你……和你爸乖乖的在家等着吧。”
“嘟…嘟…嘟…”
忙音响起,冰冷而决绝。
我维持着接电话的姿势,僵在原地,好像变成了一尊雕塑。手表屏幕暗了下去,窗外淅沥的雨声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仿佛全世界都只剩下这令人心烦意乱的声音。
母亲所在的包厢门被拉开时,梅姐正像一头警觉的猎犬,立刻从休息区的沙发上弹起,脸上堆起精心练习过的、带着谄媚与关切的笑容,快步迎了上去。
“王总,您出来啦?”她微微躬着身,声音放得又轻又柔,“今晚…还满意吗?我们雪峰是新人,有什么伺候不周到的地方,您多包涵。”
王总脸上泛着酒足饭饱后的油光,神情慵懒而满足。他慢条斯理地整理着价值不菲的腕表,瞥了梅姐一眼,从鼻子里哼出一声轻笑。
“满意,当然满意。”他的语调拉长,带着一种品鉴完佳肴后的回味,“新人?呵,有点意思。放不开,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梅姐心里松了口气,脸上的笑容更盛:“您满意就好,满意就好!她那大奶子也是极品啊!我回头再好好调教一下她,教教床技,保证您下次来,更…”
她的话没说完,王总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极其得意的事情,脸上的慵懒被一种混杂着炫耀和恶意的神采取代。他凑近梅姐,压低了声音,但那音量恰好足以让近处的人听清,语气里是掩藏不住的兴奋:
“梅姐,知道一个有意思的事吗?”他嘴角咧开一个恶劣的弧度,“前阵子,我跟上面那位领导弄的那个市政项目,不是出了点岔子吗?”
梅姐配合地露出好奇的神情。
王总得意地挑了挑眉:“总得有人出来扛事,对不对?我们就找了个合适的‘替罪羊’,一个没什么背景、偏偏还在关键文件上签过字的蠢货公务员。一撸到底,直接滚蛋了。”
他顿了顿,目光意有所指地瞟了一眼刚刚走出来的包厢方向,声音里充满了猫玩老鼠般的戏谑:
“巧了不是?刚才里面那位,就是那倒霉蛋的老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倒好,根本没认出我…哈哈哈…”他发出低沉而快意的笑声,“我是特意来尝尝他那熟女老婆的滋味,啧啧,果然…人妻别有一番征服感啊。这可比玩那些小姑娘刺激多了。”
梅姐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一瞬,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但立刻被更深的谄媚所覆盖。她迅速调整表情,顺着王总的话奉承道:“哎呦,王总,您可真是…有眼光,会玩!这都是缘分,缘分啊!说明她老公就是个绿帽废物,她就该是您的玩具…”
王总享受着这种将他人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快感,拍了拍梅姐的肩膀:“这婊子,给我留好了。下次来,我还点她。”
“一定一定!您放心!”梅姐连声保证。
王总志得意满地大笑着,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朝着会所更奢华的区域走去。
包厢内,对此一无所知的母亲,正蜷缩在沙发角落,默默地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衣衫和几乎崩溃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