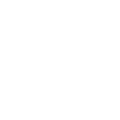14.韩月和妇姽以及他们的后来发生了什么?
帐篷里很暗。
那盏油灯还在烧,火苗比刚才更小了,小得像一颗黄豆,在那一片昏黄的光里一跳一跳的。光外面是黑,很黑很黑的黑,黑得那帐篷的角落都看不清,黑得那兽皮上的狼毛都融进去,黑得只能看见眼前这一小圈——那一盆已经凉透的水,那一块扔在地上的布,那一张铺在兽皮上的星图,还有我们三个人。
我坐在那块狼皮上。
母亲坐在我身边。
阿依兰站在我们面前。
她没敢坐。
只是站在那儿,站在那盏油灯的光能照到的地方,站在那一片昏黄的亮里。那光从下往上打,打在她脸上,把她那张脸照得半明半暗——那下巴亮亮的,那眼睛藏在阴影里,那鼻梁像一道小山,把那光分成两半。
那件青色的旧衣服在那光里更旧了,更暗了,可那被撑得鼓鼓的胸还是鼓鼓的,把那前襟绷得紧紧的,绷得那布上的梅花都变形了,一朵一朵的,歪歪扭扭的,像要掉下来。那细细的腰还是细细的,被那根布带子勒着,勒得那带子都快嵌进肉里。那浑圆的臀还是浑圆的,把那裙子后面撑得满满的,满得那裙子的褶子都撑平了,光溜溜的,在那昏黄的亮里泛着微微的光。
她低着头。
不敢看我们。
只能看见她那黑黑的头发,那亮亮的银簪,那微微发抖的肩膀。
我开口。
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尽量放轻一点。
“坐。”
她愣了一下。
抬起头。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望着我。那望里有什么东西——是意外?是不敢?
“坐下说话。”我说,“站着累。”
她又愣了一下。
然后慢慢坐下来。
坐在我们对面的地上。
那动作很慢。
很轻。
像一朵云落下来。
她坐下来的时候,那青色的裙子在她身边铺开,铺成一片,像一汪水。那两只绣花鞋从裙子底下露出来一点,那两只红色的蝴蝶在那昏黄的亮里一颤一颤的,像要飞起来。她的手放在膝盖上,那手白白的,细细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那戒指在那光里一闪一闪的。
她坐好了。
抬起头。
望着我们。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我望着她。
望着这张年轻的脸。
“阿依兰——”我说,“刚才在外面,人多,不好细问。现在你慢慢说,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她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轻。
“是。”她说。
我顿了顿。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你说现在是大夏王朝。那以前呢?以前是什么朝代?”
她望着我。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是奇怪?是“这都不知道”的那种光?
可那光只是一闪。
一闪就没了。
然后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回主子——”她说,“以前是大虞王朝。”
大虞。
那一个字像一根针。
大虞?
历史上有个大虞吗?
虞朝?那是传说里的,舜的那个朝代。可那是虞,不是大虞。
大虞——
我没听过。
我转过头。
望了母亲一眼。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和我一样——是困惑,是“这又是什么”的那种光。
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大虞王朝——”我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想了想。
那眉头微微皱起来,皱得那眉心有两道浅浅的竖纹。那纹在那白白的皮肤上,像两笔淡淡的墨。
“奴婢也说不太准。”她说,“只知道大虞传了很久,传了二十多个皇帝。最后一个皇帝叫——”
她停下来。
又想了一会儿。
“叫虞哀帝。”她说,“哀帝没有年号,因为他是亡国之君。”
虞哀帝。
那三个字像三块石头。
虞哀帝。历史上有个哀帝吗?汉朝有个哀帝,叫刘欣。唐朝有个哀帝,叫李柷。可那是汉哀帝、唐哀帝,不是虞哀帝。
虞——
我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没有。
一个都没有。
“然后呢?”我问,“大虞是怎么亡的?”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是奇怪?是“你们怎么连这都不知道”的那种光?
可她还是开口了。
那声音轻轻的。
“大虞是内乱亡的。”她说,“二十多年前,大虞朝老皇帝重病,几个皇子内乱,到处都是造反的,到处都是打仗的。朝廷管不了,各地的军阀就起来了,你打我,我打你,打了很多年。”
她顿了顿。
“后来,有一个军阀打赢了。”
“谁?”
“现在的皇帝。”她说,“绍武皇帝。”
绍武皇帝。
韩月。
那四个字又浮上来。
我望着阿依兰。
“他是哪儿的人?”我问,“什么出身?”
“回主子——”她说,“绍武皇帝是大虞朝安西镇守司的统领,西凉王。”
安西镇守司。
那六个字像六颗小石子。
安西。那是西域。镇守司——那是管边防的。
“统领?”我问,“多大的官?”
阿依兰摇摇头。
“奴婢也说不太准。”她说,“只知道他管着安西那一带的兵,手下有很多人,当年灭龟滋,破波斯,三灭塞人部族。大虞内乱的时候,他带着兵从安西打出来,一路往东打,打了很多胜仗。”
她想了想。
又说。
“他先打的是凉州。”
凉州。
那两个字让我心里一动。
凉州。她去过的那个凉州。
“然后呢?”我问。
“然后——”她说,“他一路打过去,打了很多地方。关中的那些军阀都打不过他,一个一个都降了。他收了他们的兵,越来越强。后来——”
她停下来。
那眼睛望着我。
那望里有什么东西——是害怕?还是别的什么?
“后来怎么了?”我问。
“后来——”她说,“他打到王城了。”
“王城?”
“嗯。”她说,“大虞的王城,叫朝歌。”
朝歌。
那两个字像两颗雷。
朝歌。
那是商朝的都城。纣王的那个朝歌。可那是三千多年前的事了。
朝歌——
我脑子里嗡嗡的。
阿依兰继续说。
“他打到朝歌的时候,朝里已经乱成一团了。皇帝换了好几个,最后剩下的是老皇帝的三皇子虞景炎,但最后还是输了。。。”
她顿了顿。
“然后,他就进城了。”
“进城之后呢?”
“进城之后——”她说,“他没杀老皇帝,而是扶持了个傀儡。说自己是来‘清君侧’的,是来杀那些坏大臣的。他把那些大臣杀了一批,换了一批自己的人。然后让皇帝封他做大官,管所有的事。”
我听着。
听着这些话。
那些话在我脑子里变成一幅画——一个从边关来的军阀,带着兵打进都城,杀了旧臣,换了新人,留着皇帝当傀儡,自己掌大权。
这幅画我见过。
在书里。
在历史书里。
那是——
“后来呢?”我问。
“后来——”阿依兰说,“过了几年,他就让傀儡皇帝禅位了。”
禅位。
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
“皇帝让给他了?”
“嗯。”她说,“哀帝下诏书,说自己无德无能,要把皇位让给摄政王韩月。陛下推了三次,最后才接下。然后就改国号为大夏,年号绍武。”
推了三次。
那是老套路了。
我望着阿依兰。
望着她那大大的眼睛,那黑黑的瞳孔。
“那哀帝呢?”我问,“那个让位的皇帝,后来怎么样了?”
阿依兰低下头。
那声音更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她说,“听说禅位之后没多久就病了,病了几个月,就死了。”
病死的。
那三个字在那昏黄的亮里飘着,像几片枯树叶。
我望着阿依兰。
望着她那低下去的头,那微微发抖的肩膀。
我知道那“病死的”是什么意思。
历史上那些禅位的皇帝,有几个是真正病死的?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从喉咙里进去,一直凉到心里。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阿依兰——那现在的大夏,有多大?”
她抬起头。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望着我。
“很大。”她说,“很大很大。”
“多大?”
她想了想。
那眉头又皱起来,皱得那眉心有两道浅浅的竖纹。
“奴婢也说不太准。”她说,“只知道很大。西边——”
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细细的,在那昏黄的亮里划了一下。
“西边到波斯。”
波斯。
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
波斯。那是伊朗。那是中东。那是离这儿几千里的地方。
“波斯?”我问,“那是哪儿?”
“回主子——”她说,“是西域再往西。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信的神也不一样。可那里是大夏的属国,年年要来朝贡的。”
属国。
朝贡。
我脑子里嗡嗡的。
“东边呢?”我问。
“东边到朝鲜。”
朝鲜。
那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
朝鲜。那是朝鲜半岛。那是东北亚。
“北边呢?”
“北边到北海。”
北海。
那是什么地方?贝加尔湖?还是更北的地方?
“南边呢?”
“南边到海岛。”
海岛。
那是南海?那是东南亚的那些岛屿?
我听着。
听着这些话。
那些话在我脑子里变成一张地图——一张很大的地图,西到波斯,东到朝鲜,北到北海,南到海岛。
那几乎——
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话。
我开口。
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轻轻的。
“妈——这和我们世界里清朝的版图差不多。”
母亲愣了一下。
“清朝?”
“嗯。”我说,“清朝最盛的时候,西边到中亚,东边到朝鲜,北边到西伯利亚,南边到南海。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顿了顿。
“外加一部分南海的岛屿。”
母亲没说话。
只是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在动——在转,在想。
阿依兰在旁边听着。
听着我们说话。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是奇怪?是“清朝是什么”的那种光?
可她没问。
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我们。
我转回头。
望着她。
“阿依兰——”我说,“那青藏高原呢?这儿——大夏管不管?”
她点点头。
“管的。”她说,“有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
那四个字像四根针。
驻藏大臣。那是清朝的制度。清朝在西藏设驻藏大臣,管着那一带的事。
可这儿——
我望着阿依兰。
“驻藏大臣管什么?”
“管收税。”她说,“还有——有时候管管那些大的纠纷。别的不管。”
“别的不管?”
“嗯。”她说,“这儿太远了,山太多,路太难走。驻藏大臣一年也来不了几次。来了也就是收收税,见见各部的头人,然后就走了。平时这儿的事,还是各部自己管。”
我听着。
听着这些话。
那些话在我脑子里拼成一幅画——一个遥远的边疆,一个名义上归朝廷管、实际上自己说了算的地方。朝廷派个大臣来,收点税,走个过场,然后就走了。剩下的,还是那些土司、那些头人、那些部落自己管。
这和我们那个世界里的西藏,差不多。
可又不一样。
不一样在——
我抬起头。
望着阿依兰。
“阿依兰——”我说,“大夏有多少年了?”
她想了想。
“绍武皇帝登基到现在——”她算着,“有43年了。”
43年。
那三个字像三块石头。
43年。
那也就是说,大夏王朝才成立了43年。
那大虞呢?大虞有多少年?
我没问。
只是坐在那儿。
脑子里嗡嗡的。
嗡嗡的。
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飞。
阿依兰还坐在那儿。
坐在那昏黄的亮里。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望着我们。那望里有什么东西——是奇怪?是好奇?还是那种“你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的光?
可她还是没问。
只是坐在那儿。
等着。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阿依兰——那个绍武皇帝,他叫什么来着?”
“韩月。”她说,“叫韩月。”
韩月。
那两个字又浮上来。
我望着她。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她愣了一下。
那眼睛瞪得大大的。
“男的啊。”她说,“当然是男的。”
男的。
韩月。
一个男的皇帝叫韩月。
历史上有个叫韩月的男皇帝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困惑,有惊骇,有那种“这不可能”的光。
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更轻了。
“阿依兰——那个韩月,他长什么样?”
她想了想。
那眉头又皱起来。
“奴婢没见过。”她说,“只听人说过。听说——”
她停下来。
“听说什么?”
“听说——”她说,“听说他长得很好看。”
好看。
那两个字像两根针。
“怎么个好看法?”
“听说是——”她说,“面如冠玉,目若朗星。个子很高,喜欢穿白衣服。骑一匹白马,拿一杆银枪。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敌人看见他就怕。”
面如冠玉。
目若朗星。
白衣服。
白马。
银枪。
那是一个将军的形象。
一个很能打的将军。
一个从边关打出来的将军。
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
转得很快。
快得像那年逃出那个小县城的时候——那种快。
大虞朝内乱。
安西镇守司统领。
带兵打进王城。
杀大臣。
换新人。
留皇帝当傀儡。
最后让皇帝禅位。
自己当皇帝。
这一套——
这一套我见过。
在书里。
在历史书里。
那是——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从喉咙里进去,一直凉到心里。
然后我开口。
那声音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可那轻轻里,有东西。
有那个让我心里发冷的东西。
“阿依兰——”我说,“你说的那个绍武皇帝,他当初打进王城的时候,杀的那些大臣,换的那些新人,留着的那个皇帝——他这套做法,叫什么?”
她愣了一下。
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叫什么?”她重复着,像没听懂。
“历史上——”我说,“这种人,叫什么?”
她想了想。
摇摇头。
“奴婢不知道。”她说,“奴婢只知道他赢了。”
赢了。
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
是啊。
他赢了。
赢了就是皇帝。
输了就是反贼。
就这么简单。
我坐在那儿。
坐在那块狼皮上。
脑子里嗡嗡的。
嗡嗡的。
母亲的手伸过来。
握住我的手。
那手热热的,软软的,紧紧的。
我转过头。
望着她。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话。
那话是——
“别怕。”
我握紧她的手。
握得紧紧的。
紧紧的。
然后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望着这个坐在昏黄亮里的、从凉州回来的、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的女人。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更轻了。
“阿依兰——那个韩月,他是什么时候打进王城的?”
“50年前吧?不清楚呀。”她说,“那时候奴婢还没出生呢。”
50年前。
那也就是说,50年前,那个叫韩月的人,带着兵从安西打出来,一路往东打,打了很多仗,最后打进朝歌,杀了很多人,换了很多人,留了一个小皇帝当傀儡,最后自己当了皇帝。
那套做法——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说。
那话从嘴里出来,轻轻的,像对自己说的。
“这不就是成功版本的董卓吗?”
母亲愣了一下。
望着我。
“董卓?”
“嗯。”我说,“东汉末年,董卓也是从边关打进来的,也是杀大臣换新人,也是留皇帝当傀儡。可董卓最后失败了,被人杀了。这个韩月——”
我停下来。
望着那跳动的灯火。
“他赢了。”
帐篷里很静。
很静很静。
只有那油灯的火苗在跳,一跳一跳的,把那光一晃一晃的。
阿依兰坐在那儿。
望着我们。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是奇怪?是“董卓是谁”的那种光?
可她没问。
只是坐在那儿。
等着。
母亲的手还握着我的手。
握得紧紧的。
她的手心有点潮——是汗。
我握紧她的手。
然后我开口。
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沉沉的。
“阿依兰——”
“奴婢在。”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大大的眼睛,那黑黑的瞳孔,那瞳孔里跳动的灯火。
“谢谢你。”我说,“你说的这些,对我们很有用。”
她愣了一下。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是意外?是不敢相信?
然后她低下头。
那声音轻轻的。
“奴婢不敢。”她说,“能为主子分忧,是奴婢的福分。”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低下去的头,那弯下去的脖子,那微微发抖的肩膀。
帐篷里很静。
那盏油灯的火苗还在跳,一跳一跳的,把那光一晃一晃的。光外面是黑,很黑很黑的黑,黑得那帐篷的角落都看不清,黑得只能看见眼前这一小圈——那一张铺在兽皮上的星图,那一盆已经彻底凉透的水,还有我们三个人。
阿依兰已经站起来了。
可母亲没让她走。
母亲的手还握着我的手,握得紧紧的。可她转过头,望着阿依兰,那眼睛亮亮的,那亮里有话。
“阿依兰——”母亲开口了。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可那轻轻软软里,有东西。是那种“我还要问”的东西。
阿依兰停下来。
站在帐篷门口。
那帘子还在她手里,掀开一半,外面的夜风从那缝隙里灌进来一点,凉凉的,把她那青色的裙子吹得一飘一飘的。那裙摆飘起来,露出下面那细细的脚踝,那脚踝上系着的红绳,那红绳在那昏黄的亮里,像一道细细的血线。
她望着母亲。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神女还有什么吩咐?”她问。
母亲望着她。
望着她那张年轻的脸,那被夜风吹得一飘一飘的裙子,那站在门口、半明半暗的身子。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母亲说。
阿依兰点点头。
她把帘子放下来。
那帘子落下的时候,外面的夜风被挡住了,帐篷里又静下来,只有那油灯的火苗在跳,一跳一跳的。
她走回来。
又坐在我们对面。
坐在那昏黄的亮里。
那动作还是那么慢,那么轻,像一朵云落下来。她坐下来的时候,那青色的裙子在她身边铺开,铺成一片,像一汪水。那两只绣花鞋从裙子底下露出来一点,那两只红色的蝴蝶在那昏黄的亮里一颤一颤的,像要飞起来。
她坐好了。
抬起头。
望着母亲。
母亲望着她。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话。
“阿依兰——”母亲说,“你说现在是绍武皇帝,叫韩月。他登基十三年了。那他今年多大岁数?”
阿依兰愣了一下。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是意外?是“怎么问这个”的那种光?
可那闪只是一闪。
一闪就没了。
然后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
“回神女——”她说,“今年是绍武四十五年。”
绍武四十五年。
那六个字像六块石头。
我愣了一下。
四十五年?
刚才不是说登基十三年吗?
我望着阿依兰。
“你不是说登基十三年吗?”我问。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回主子——”她说,“登基是十三年。可绍武皇帝掌权是——”
她停下来。
算了算。
那眉头微微皱起来,皱得那眉心有两道浅浅的竖纹。
“是四十八年。”她说,“陛下今年——掌权四十八年了。”
四十八年。
那四个字像四颗雷。
我脑子里嗡嗡的。
登基十三年,掌权四十八年——那也就是说,他在当皇帝之前,已经掌权三十五年了。
那三十五年,他是以什么身份掌权的?
摄政王?
权臣?
还是那个“留着皇帝当傀儡”的人?
我望着阿依兰。
“那他今年多大岁数?”母亲又问了一遍。
阿依兰抬起头。
望着母亲。
“回神女——”她说,“陛下今年七十岁了。”
七十岁。
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
七十岁。
那个从安西打出来的将军,那个面如冠玉、目若朗星的人,那个喜欢穿白衣服、骑白马、拿银枪的人——七十岁了。
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穿着白衣服,骑着白马,拿着银枪。那画面有点怪,有点不协调。可那画面只是一闪,一闪就没了。
母亲继续问。
那声音还是轻轻的,软软的。
“陛下册封太子了吗?”
阿依兰摇摇头。
那摇很慢。
很轻。
“没有。”她说。
没有太子。
那两个字像两根针。
我望着阿依兰。
“为什么没有?”我问。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那望里有什么东西——是犹豫?是不知道该不该说的那种光?
“说。”我说,“没事。”
她低下头。
那声音更轻了。
“因为——”她说,“因为皇后。”
“皇后?”
“嗯。”她说,“皇后妇姽。”
妇姽。
那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
这名字有点怪。妇姽——妇是妇人,姽是姽婳,意思是娴静美好。可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听起来不像名字,像——
“皇后怎么了?”母亲问。
阿依兰抬起头。
望着母亲。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
“皇后——”她说,“是陛下的母亲。”
那七个字像七颗雷。
炸在我脑子里。
母亲?
陛下的母亲?
那个七十岁的皇帝的——母亲?
我愣住了。
望着阿依兰。
望着她那大大的眼睛,那黑黑的瞳孔。
“你说什么?”我问,“皇后是——陛下的母亲?”
阿依兰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轻。
“嗯。”她说,“皇后妇姽,是陛下的生母。”
生母。
那两个字像两块烧红的铁。
烙在我心上。
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和我一样——是惊骇,是不信,是那种“这怎么可能”的光。
我们俩的故事。
一模一样。
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哑哑的。
“那——那她是怎么成为皇后的?”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在讲一个故事。
“皇后妇姽——”她说,“当年是大虞朝安西镇北司的都统。”
安西镇北司。
那六个字像六颗小石子。
都统。
那是带兵的。
女的带兵的。
“她是大虞朝最强的女将军。”阿依兰说,“那时候,安西那一带,没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带着兵,打过很多仗,打过西域,打过匈奴,打过那些造反的人。她的旗子插到哪里,哪里就投降。”
我听着。
听着这些话。
那些话在我脑子里变成一幅画——一个女人,穿着盔甲,骑着马,拿着刀,带着兵,在战场上冲杀。那女人很强,很强,强得所有人都怕她。
“后来呢?”母亲问。
“后来——”阿依兰说,“她嫁人了。”
“嫁给谁?”
“嫁给安西镇守司的一个将军。”阿依兰说,“那个将军就是后来的绍武皇帝的父亲。可那将军命短,没几年就死了。留下她和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就是韩月。
我听着。
脑子里嗡嗡的。
“然后呢?”母亲问。
“然后——”阿依兰说,“她就一个人带着儿子,继续带兵。她儿子长大了,也当了兵,也成了将军。后来——”
她停下来。
望着我们。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
“后来怎么了?”我问。
“后来——”她说,“她嫁给她儿子了。”
那七个字像七把刀。
扎在我心上。
嫁给她儿子了。
嫁给她儿子了。
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在抖。
在抖。
在抖。
我握紧她的手。
握得紧紧的。
紧紧的。
然后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更哑了。
“为什么?”
阿依兰摇摇头。
“奴婢不知道。”她说,“只知道他们成亲了。那时候,她儿子已经是安西镇守司的统领了,手里有兵,有权。他们成亲之后,就更强了。后来——”
她顿了顿。
“后来他就带着兵打出来了。”
我听着。
听着这些话。
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着,转着,转成一团乱麻。
母亲的手在我手里发抖。
那抖很轻。
可我能感觉到。
我握紧她的手。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那——那他们有孩子吗?”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有几个,可是。。。”她说。
那一个字像一根针。
“可是什么?”
“嗯。”她说,“可是他们的长子,其实——”
她停下来。
那脸上的表情很怪。
“长子怎么了?是太子吗?”
阿依兰低下头。
那声音更轻了。
“不不不,那位——”她说,“不是陛下的种。”
不是陛下的种。
那六个字像六块石头。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阿依兰抬起头。
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犹豫,有害怕,有那种“不知道该不该说”的光。
“说。”我说,“没事。”
她深吸一口气。
那气轻轻的。
然后她开口。
“皇后妇姽——”她说,“当年,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陛下的妻子。”
“什么意思?”
“那时候——”阿依兰说,“陛下是摄政王,掌着大权。可那时候的皇帝,还是大虞的皇帝。大虞最后一个皇帝——”
她停下来。
望着我。
“虞昭。”她说,“就是虞哀帝。”
虞昭。
那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
“虞昭怎么了?”母亲问。
阿依兰望着母亲。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虞昭——”她说,“是皇后的丈夫。”
那七个字像七颗雷。
炸在我脑子里。
皇后的丈夫?
那个皇后的丈夫不是韩月吗?
她不是嫁给韩月了吗?
怎么又出来一个虞昭?
我望着阿依兰。
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沙沙的。
“你是说——皇后妇姽,先嫁给了韩月,然后又嫁给了虞昭?”
阿依兰摇摇头。
“不是。”她说,“是先嫁给虞昭,再嫁给陛下。”
先嫁给虞昭。
再嫁给陛下。
那八个字在我脑子里转着。
转着。
转成一团乱麻。
“等等——”我说,“你刚才不是说,皇后嫁给陛下了吗?怎么又变成先嫁给虞昭了?”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回主子——”她说,“是这样——陛下当年是摄政王,皇后是他母亲,也是他妻子。可后来——”
她停下来。
又吸了一口气。
“后来,陛下为了让自己的权力更稳,就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他让皇后——”阿依兰说,“和自己离婚。”
离婚。
那两个字像两根针。
“离婚?”
“嗯。”她说,“然后,他把妻子嫁给了虞昭。”
嫁给虞昭。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虞昭是皇帝?”我问。
“是。”她说,“那时候的皇帝,是虞昭。他才十几岁。”
十几岁的皇帝。
嫁给他。
把母亲兼妻子嫁给他。
我脑子里嗡嗡的。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阿依兰摇摇头。
“奴婢也不知道。”她说,“只知道他那么做了。那时候,他是摄政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把皇后嫁给了虞昭,虞昭就封皇后为皇后——大虞的皇后。”
大虞的皇后。
那个女人,先是将军,然后是韩月的母亲,然后是韩月的妻子,然后又是虞昭的皇后。
这——
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已经不会抖了——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的光。
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然后呢?”
“然后——”阿依兰说,“皇后就住在宫里,和虞昭在一起。过了——大概一年多吧。然后——”
她停下来。
“然后怎么了?”
“然后——”她说,“她就怀孕了。”
怀孕了。
那两个字像两块烧红的铁。
“怀的谁的?”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是虞昭的。”她说。
是虞昭的。
那四个字像四把刀。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呢?孩子生下来了?”
“生下来了。”阿依兰说,“是个男孩。”
男孩。
“那个男孩呢?”
“活着。”阿依兰说,“现在还在。”
还在。
“在哪儿?”
“在皇宫里。”阿依兰说,“陛下养着的。”
陛下养着的。
那个虞昭的孩子。
那个不是他种的孩子。
他养着的。
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
转得很快。
“然后呢?”母亲问,“皇后生了那个孩子之后呢?”
阿依兰望着母亲。
“之后——”她说,“陛下就废了虞昭。”
废了虞昭。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怎么废的?”
“和后来废哀帝一样。”阿依兰说,“让虞昭禅位。虞昭禅位之后,就——死了,听说是因为贫穷,冻死在皇都的贫民窟里。”
死了。
那两个字像两根针。
“然后呢?”
“然后——”阿依兰说,“陛下又把皇后娶回来了。”
又娶回来了。
那五个字像五颗雷。
“娶回来之后呢?”
“册为皇后。”阿依兰说,“就是现在的皇后。那个虞昭的孩子,也跟着回来了,养在宫里。对外——”
她停下来。
“对外怎么说?”
“对外——”阿依兰说,“说是陛下的儿子。可每个人都知道不是。”
每个人都知道不是。
那八个字像八块石头。
我坐在那儿。
坐在那块狼皮上。
脑子里嗡嗡的。
嗡嗡的。
母亲的手在我手里。
那手已经不抖了。
可那手心全是汗。
全是汗。
阿依兰还坐在那儿。
坐在那昏黄的亮里。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望着我们。
等着我们问。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那——那个孩子,现在多大了?”
阿依兰想了想。
“应该——”她说,“应该50多了吧。虞昭是47多年前被废的,那孩子是废之前生的,算起来——”
她算了算。
“55岁。是个老太子了。”
55岁。
那也就是说,那个孩子,比我还大,比母亲还年长,算是个老爷爷了。
我望着阿依兰。
“那个孩子,叫什么?”
“叫韩琮。”阿依兰说,“陛下给取的名字。”
韩琮。
那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
“他有资格当太子吗?”母亲问。
阿依兰望着母亲。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
“有——”她说,“也没有。”
“什么意思?”
“有——”阿依兰说,“是因为陛下养着他,对外说他是陛下的儿子,那他就是皇子,就有资格。没有——”
她停下来。
“没有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不是陛下的种。那些大臣,那些勋贵,那些后宫的娘娘们,都知道。所以他们——”
“他们怎么了?”
“他们——”阿依兰说,“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太子。”
自己的儿子。
那四个字像四根针。
“陛下还有别的儿子?”我问。
“有。”阿依兰说,“很多。”
很多。
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
“都有谁?”
阿依兰想了想。
那眉头皱起来,皱得那眉心有两道浅浅的竖纹。
“最有权势的——”她说,“是贵妃薛敏华的儿子。”
薛敏华。
那三个字像三颗小石子。
“薛敏华是谁?”
“是安西勋贵家族的人。”阿依兰说,“她是安西那边的大贵族,当年跟着陛下一起打出来的。她一直帮助陛下处理财物问题,很早就认识陛下,后来进了宫,封了贵妃,生了一个儿子,叫韩璋。”
韩璋。
“多大了?”
“50出头吧。”阿依兰说,“听说很聪明,很会打仗,陛下很喜欢他。”
我听着。
脑子里记着。
“还有呢?”
“还有贵妃玄悦。”阿依兰说,“她也是安西勋贵家族的,和薛敏华一样。她也有一个儿子,叫韩珺。40多岁了吧,听说也很能干,当年朝鲜叛乱就是他平定的。”
韩珺。
“这两个贵妃关系怎么样?”
阿依兰摇摇头。
那摇很轻。
可那轻轻里,有东西。
“很差。”她说,“非常差。”
“为什么?”
“因为——”阿依兰说,“她们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而且——”
她停下来。
“而且什么?”
“而且——”阿依兰说,“她们和皇后的关系也很差。”
皇后。
妇姽。
那个既是母亲又是妻子又是前朝皇后的人。
“为什么差?”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因为——”她说,“皇后是陛下的母亲。”
那七个字又浮上来。
“那些贵妃——”阿依兰说,“她们年轻,她们漂亮,她们有自己的家族撑腰。可皇后——皇后有陛下。陛下什么都听她的。那些贵妃再怎么争,也争不过她。”
我听着。
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一个七十岁的老皇帝,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妻子的皇后,一群年轻漂亮的贵妃,一堆想当太子的儿子。那些人斗成一团,斗得你死我活。
“还有别人吗?”母亲问。
阿依兰点点头。
“有。”她说,“还有公孙昭仪。”
公孙昭仪。
“她是哪儿的人?”
“辽东的。”阿依兰说,“不是安西勋贵家族的。是后来陛下打辽东的时候,收的。她家里也是大贵族,在那边很有势力。她也有一个儿子,叫韩玦。”
韩玦。
“她和皇后关系怎么样?”
阿依兰摇摇头。
“也很差。”她说,“非常差。她和那两个贵妃也不和。她们4个人——”
她停下来。
那脸上的表情很怪。
“她们怎么了?”
“她们——”阿依兰说,“斗得可厉害了。奴婢在凉州的时候,就听说过。她们互相害,互相下毒,互相在陛下面前说坏话。听说——”
她压低声音。
那声音更轻了。
“听说薛贵妃的孩子,死过一个。”
死过一个。
那四个字像四把刀。
“怎么死的?”
“不知道。”阿依兰说,“有人说是玄贵妃害的,有人说是公孙昭仪害的,还有人说是——”
她停下来。
“说是谁?”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说是皇后。”她说。
皇后。
那个既是母亲又是妻子的人。
害死了贵妃的孩子。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惊骇,有不解,有那种“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的光。
我握紧她的手。
然后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阿依兰——那皇后,她——她后来没再生吗?”
阿依兰愣了一下。
“再生?”
“嗯。”我说,“她不是陛下的皇后吗?后来——没再怀过孕吗?”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那望里有什么东西——是奇怪?是“这也要问”的那种光?
然后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
“回主子——”她说,“怀过。”
怀过。
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
“怀过几次?”
“好几次。”阿依兰说。
好几次。
那三个字像三根针。
“那——孩子呢?”
阿依兰低下头。
那声音更轻了。
“都没活下来。”
都没活下来。
那五个字像五块石头。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低下去的头,那微微发抖的肩膀。
“为什么?”
阿依兰抬起头。
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害怕,有犹豫,有那种“不知道该不该说”的光。
“说。”我说,“没事。”
她深吸一口气。
那气轻轻的。
然后她开口。
“听说是——”她说,“那些贵妃们害的。”
那些贵妃们害的。
那七个字像七把刀。
我脑子里嗡嗡的。
“害的?”
“嗯。”阿依兰说,“皇后怀了好几次,每一次都——要么是流产,要么是生下来就死。听说有一次,孩子都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好好的,可没过三天就死了。”
三天就死了。
那四个字像四根针。
“怎么死的?”
“不知道。”阿依兰说,“有人说是被人捂死的。”
捂死的。
那三个字像三块烧红的铁。
我坐在那儿。
脑子里嗡嗡的。
嗡嗡的。
母亲的手在我手里。
那手又抖起来了。
抖得很轻。
可我能感觉到。
我握紧她的手。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那——陛下不管吗?”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管。”她说,“可管不住。”
管不住。
那三个字像三块石头。
“为什么管不住?”
阿依兰摇摇头。
“因为——”她说,“那些贵妃们,背后都有家族。她们的父亲、兄弟,都是大夏的功臣,都握着兵权,都管着地方。陛下再怎么查,也查不出什么。就算查出来了,也不能把她们怎么样。”
不能把她们怎么样。
那七个字像七根针。
我望着阿依兰。
望着她那大大的眼睛,那黑黑的瞳孔。
“那皇后呢?”我问,“皇后就——认了?”
阿依兰摇摇头。
那摇很轻。
可那轻轻里,有东西。
“皇后不认。”她说,“皇后一直在斗。”
一直在斗。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怎么斗?”
“她——”阿依兰说,“她也害她们。听说,薛贵妃的一个孩子,就是她害死的。玄贵妃也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听说也是她害的。公孙昭仪更惨——”
她停下来。
“公孙昭仪怎么了?”
“公孙昭仪——”阿依兰说,“生过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活下来了,长到三岁,有一天在御花园里玩,掉进水里,淹死了。”
淹死了。
那三个字像三根针。
“是皇后害的?”
阿依兰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轻。
“都这么说。”她说。
都这么说。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我坐在那儿。
脑子里嗡嗡的。
嗡嗡的。
那幅画越来越清楚了——一个七十岁的老皇帝,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妻子的皇后,一群年轻漂亮的贵妃,一堆想当太子的儿子。那些人斗成一团,斗得你死我活。皇后害死了贵妃的孩子,贵妃害死了皇后的孩子。那宫里全是血,全是仇,全是死人。
这就是大夏王朝。
这就是那个从安西打出来的绍武皇帝的家。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惊骇,有恐惧,有那种“我们该怎么办”的光。
“阿依兰——”母亲说,“你刚才说,皇后怀过好几次,都没活下来。是每一次都没活下来吗?还是——”她停下来。
那话没说完。
可那没说完的话,我们都懂。
阿依兰望着母亲。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
“回神女——”她说,“不是每一次都没活下来。皇后——其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
那两个字像五块石头。
我愣了一下。
五个?
刚才不是说都没活下来吗?
我望着阿依兰。
“五个?”我问,“你是说,有五个孩子出生了?”阿依兰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轻。
“嗯。”她说,“五个。陛下很宠皇后,一直让她怀。前前后后——”她停下来。
算了算。
那眉头微微皱起来,皱得那眉心有两道浅浅的竖纹。
“七八次吧。”她说,“流产了很多次。可也有五个生下来了。”七八次。
流产很多次。
生下来五个。
那些数字在我脑子里转着。
我望着阿依兰。
“那五个孩子呢?都活着吗?”阿依兰摇摇头。
那摇很慢。
很轻。
“没有。”她说,“只活下来一个。”只活下来一个。
那六个字像六根针。
“那四个呢?”“三个夭折了。”阿依兰说,“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一个生下来没几个月就死了,一个一岁多死的,一个三岁多死的。还有一个——”她停下来。
那脸上的表情很怪。
“还有一个怎么了?”“还有一个——”阿依兰说,“有很严重的病。”严重的病。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什么病?”“不知道。”阿依兰说,“只知道一直病着,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活倒是活着,可跟死了也差不多。”我听着。
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一个躺在床上的孩子,不会动,不会说话,就那么躺着,躺着,躺了很多年。
“那个孩子多大了?”母亲问。
阿依兰想了想。
“应该——”她说,“三十多了吧。比长公主小一点。”长公主。
那三个字像三颗小石子。
“长公主?”我问,“谁是长公主?”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就是那个活下来的。”她说,“皇后的第五个孩子。建宁长公主,韩菲雪。”建宁长公主。
韩菲雪。
那六个字像六颗星星。
“她活下来了?”母亲问。
“嗯。”阿依兰说,“她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她停下来。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是羡慕?是惊叹?还是别的什么?
“而且什么?”“而且——”阿依兰说,“她很健康。身体特别好。从小就不生病,不发烧,什么毛病都没有。长得也——”她又停下来。
“长得怎么了?”“长得——”阿依兰说,“是天下第一美人。”天下第一美人。
那六个字像六朵花。
我望着阿依兰。
“天下第一美人?”“嗯。”阿依兰说,“都这么说。说她长得像天上的仙女,说她一笑,满宫的花都开了,说她的眼睛像星星,说她的皮肤像雪,说她——”她说不下去了。
只是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向往,有崇拜,有那种“我这辈子都比不上”的光。
我听着。
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女人,很美很美的女人,美得所有人都夸,美得全天下都知道。
“她多大了?”母亲问。
阿依兰望着母亲。
“今年——”她说,“四十多了。”四十多了。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四十多岁的女人,还是天下第一美人?
我望着阿依兰。
“四十多?”“嗯。”阿依兰说,“长公主今年四十多了。可听说她看着还像二十多岁的姑娘。一点不见老。”一点不见老。
那五个字像五根针。
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
转得很快。
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阿依兰——你说皇后生了五个孩子。长公主是最小的?”“嗯。”阿依兰说,“是最小的。”“那——皇后生长公主的时候,多大岁数了?”阿依兰愣了一下。
那眼睛望着我。
那望里有什么东西——是意外?是“怎么问这个”的那种光?
然后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
“回主子——”她说,“皇后生长公主的时候——应该是五十多岁。”五十多岁。
那四个字像四颗雷。
炸在我脑子里。
五十多岁。
一个女人,五十多岁,生孩子?
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和我一样——是不信,是惊骇,是那种“这怎么可能”的光。
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那声音从喉咙里出来,哑哑的。
“你是说——皇后五十多岁的时候,还给陛下生下了长公主?”阿依兰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重。
“是。”她说。
是。
那一个字像一把锤子。
砸在我心上。
五十多岁。
生孩子。
还生下来了。
还活下来了。
还健康。
还美。
这——我脑子里嗡嗡的。
嗡嗡的。
母亲的手在我手里。
那手又抖起来了。
抖得很轻。
可我能感觉到。
我握紧她的手。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那——陛下多大?”阿依兰望着我。
“陛下比皇后小。”她说,“那时候——陛下应该四十多岁吧。”四十多岁。
男人四十多岁还能生。
女人五十多岁也能生。
这——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那长公主现在——四十多岁?”我问。
“嗯。”阿依兰说,“四十多了。”“她嫁人了吗?”阿依兰摇摇头。
“没有。”她说,“长公主一直没嫁人。”没嫁人。
那三个字像三根针。
“为什么?”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因为——”她说,“没人配得上她。”没人配得上她。
那六个字像六块石头。
我听着。
脑子里又浮现出那个画面——一个四十多岁还像二十多岁的女人,美得天下第一,谁都不嫁,因为没人配得上。
这——“那她在宫里做什么?”母亲问。
阿依兰望着母亲。
“长公主——”她说,“帮陛下处理政务。”处理政务。
那四个字像四颗小石子。
“她会处理政务?”“嗯。”阿依兰说,“长公主不仅美,还特别聪明。听说她读书过目不忘,算账比账房先生还快,看人一眼就能看出好坏。陛下很多事都问她,她也帮陛下处理了很多大事。”聪明。
美。
健康。
四十多岁。
不嫁人。
帮皇帝处理政务。
这——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转。
转得很快。
可那转没有结果。
只是一团乱麻。
我望着阿依兰。
望着她那大大的眼睛,那黑黑的瞳孔。
“阿依兰——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阿依兰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重。
“都是真的。”她说,“奴婢不敢骗主子。”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惊骇,有困惑,有那种“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光。
我握紧她的手。
握得紧紧的。
紧紧的。
然后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那——长公主和那些贵妃们关系怎么样?”阿依兰愣了一下。
然后她低下头。
那声音更轻了。
“不好。”她说,“非常不好。”非常不好。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为什么?”阿依兰抬起头。
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犹豫,有害怕,有那种“不知道该不该说”的光。
“说。”我说,“没事。”她深吸一口气。
那气轻轻的。
然后她开口。
“因为——”她说,“那些贵妃们,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可长公主——”她停下来。
“长公主怎么了?”“长公主——”阿依兰说,“不支持她们任何一个。”不支持。
那三个字像三根针。
“长公主支持谁?”阿依兰摇摇头。
“谁也不支持。”她说,“长公主只支持陛下。”只支持陛下。
那五个字像五颗小石子。
“那——那些贵妃们不恨她吗?”阿依兰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轻。
“恨。”她说,“可拿她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阿依兰说,“陛下宠她。特别宠。宠得不得了。那些贵妃们再怎么闹,也不敢动长公主。动了她,陛下会杀了她们的。”陛下会杀了她们。
那七个字像七把刀。
我听着。
脑子里又浮现出一幅画——一个四十多岁的美人,站在皇帝身边,帮他处理政务。那些贵妃们在下面斗来斗去,可谁也动不了她。因为皇帝宠她。因为她是他的女儿。因为她是那个五十多岁的母亲生下来的、唯一活下来的、健康聪明的女儿。
这——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那——长公主和皇后关系怎么样?”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很好。”她说,“非常好。”非常好。
那三个字像三朵花。
“皇后很疼长公主。长公主也很孝顺皇后。”阿依兰说,“她们母女俩,是宫里最亲的。”最亲的。
那三个字像三团火。
烧在我心里。
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变了——从惊骇变成了别的什么。是温暖?是羡慕?还是那种“我们也该那样”的光?
我握紧她的手。
握得紧紧的。
紧紧的。
然后我转回头。
望着阿依兰。
望着这个坐在昏黄亮里的、从凉州回来的、知道这么多事的女人。
那话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谢谢你,阿依兰。”阿依兰愣了一下。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是意外?是不敢相信?
然后她低下头。
那声音轻轻的。
“奴婢不敢。”她说,“能为主子分忧,是奴婢的福分。”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低下去的头,那弯下去的脖子,那微微发抖的肩膀。
然后我说。
“你回去休息吧。天快亮了。”她抬起头。
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是。”她说。
她站起来。
那动作还是那么慢,那么轻,像一朵云升起来。
她站起来的时候,那青色的裙子从地上被带起来,沙沙响,像夜风吹过草丛的声音。那两只绣花鞋在地上一转,那两只红色的蝴蝶在那昏黄的亮里一闪,一闪,然后她转过身,朝帐篷门口走去。
她走到门口。
掀开帘子。
那帘子掀开的时候,外面的夜风又灌进来一点,凉凉的,带着草原上的味道。那风吹得那油灯的火苗一晃,一晃,差点灭了。
然后帘子落下。
她出去了。
帐篷里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那油灯的火苗慢慢稳下来,又一跳一跳的,把那光一晃一晃的。
我坐在那儿。
坐在那块狼皮上。
母亲坐在我身边。
她的手还握着我的手。
握得紧紧的。
紧紧的。
我们谁也没说话。
只是坐在那儿。
望着那盏油灯。
望着那跳动的火苗。
脑子里转着那些话——皇后五十多岁生孩子。
长公主四十多岁,天下第一美人。
聪明,健康,得宠。
和那些贵妃们斗。
和皇后最亲。
那些话在我脑子里转着,转着,转成一团乱麻。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
然后我转过头。
望着母亲。
她也在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话。
那话是——“我们也会有孩子的。”我愣了一下。
望着她。
她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定。
很定。
定得像那年在出租屋里她第一次说“妈跟你走”的时候——那种定。
“妈——”我说。
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热热的。
她的手碰到我的脸。
碰到我脸上那些黑灰。
她的手在我脸上摸着。
轻轻地。
慢慢地。
摸过我的眉毛,摸过我的眼睛,摸过我的鼻子,摸过我的嘴。
然后她停下来。
停在我嘴边。
那手指按在我嘴唇上。
那手指上有她的味道——晚香玉,还有她自己那种让我头晕的味道。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那年出租屋里她第一次叫我“儿”的时候——那种声音。
“儿,”她说,“我们也会有的。”那五个字像五团火。
烧在我心里。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那嘴角的痂,那被狐毛围着的脸。
然后我说。
“嗯。”那一个字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可那轻轻里,有山。
有海。
有整个世界。
帐篷外面,夜风吹过。
呜呜的。
像在唱歌。
唱一首很老很老的歌。
那歌里有什么?
有那些死去的人?
有那些还没出生的人?
有那个五十多岁还在生孩子的皇后?
有那个四十多岁还是天下第一美人的长公主?
有我们?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母亲的手在我手里。
热热的。
软软的。
紧紧的。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