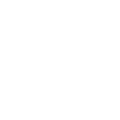17.代价是值得的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母亲走向那张案子。她的脚步很轻,赤足踩在冰凉的石板地上,那被黑丝裹着的脚趾微微蜷曲着,像是不愿直接触碰那冷。她走路的姿态还是那样,一扭一扭的,一摇一摆的,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仿佛那胯间还流着的、正顺着大腿内侧往下淌的东西不存在似的。
她走到案子前。
那案子是紫檀木的,黑沉沉的,上面摆着那两样东西——那封用红绸系着的册封文书,那厚厚的贸易许可书。旁边还有别的——几张信函,一个青瓷的笔洗,几支狼毫笔,一方端砚,砚台里还有未干的墨汁。
母亲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还沾着那胖子的口水,沾着她自己嘴里流出来的东西,黏黏的,在那昏黄的光里亮着。她没有擦。就那么伸着,拿起那两样东西。
她拿起它们的时候,那手指细细地摸着那绫子的封面,摸着那朱红的大印,摸着那大印上凹凸的纹路。那动作很慢,慢得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又慢得像在确认什么——确认这一切是真的,不是一场梦。
然后她转过身。
望着那胖子。
那胖子还跪在榻上,跪在那儿,像一堆瘫软的肉。他那敞开的便服下面,那东西软着,蔫着,垂着,那头上还沾着刚才的东西,白白的,黏黏的,在那光里泛着光。他低着头,不敢看她。那两条缝里的眼睛望着自己那软软的东西,望着那沾在上面的东西,那脸上的表情——是羞愧,是懊恼,是那种“我怎么就不行了”的丧气,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小孩子做错了事怕被大人骂的那种怕。
母亲望着他。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公孙大人——”那三个字从那嘴里出来,甜得像糖。
那胖子浑身一抖。
那抖从那胖胖的身体里传出来,像一堆肉在颤。他抬起头,望着她。那两条缝里的眼睛里,有光——是意外,是怕,是那种“她还要干什么”的不安。
“夫人——”他说,那声音闷闷的,沉沉的,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可那闷里还有别的——是讨好的那种调子,“夫人还有什么吩咐?”母亲笑了。
那笑从那嘴角溢出来,从那粉粉的新肉旁边溢出来。
“大人——”她说,“这些东西,妾身拿走了。”她晃了晃手里的文书。
那两样东西在她手里一晃,一晃的,那红绸子在那光里一闪一闪的,像一团火。
那胖子连忙点头。
那点把那脸上的肉都点得晃起来。
“拿走拿走——”他说,“本就是给狼王的。本就是给狼王的。”母亲点点头。
那一下点得很轻。
然后她把那两样东西放在案子上。
放在那儿。
她没穿衣服。
就那么光着身子,站在那案子前,站在那昏黄的光里。那背对着我,那背光滑的,白的,上面全是汗,亮亮的。那汗从背上淌下来,淌过那腰,淌过那臀,淌过那黑丝裹着的腿,滴在地上。那腰细得不像话。那臀上还有那胖子手抓出来的红印,一道一道的,在那白白的皮肤上很明显。那臀肉微微地颤着,一颤一颤的,像两团在风里的果冻。那两腿之间,有什么东西正往下淌,顺着那大腿内侧,淌过那黑丝,淌到那膝盖弯的地方,在那黑丝上留下一道亮亮的水痕。
她站在那儿。
开始穿衣服。
那动作很慢。
慢得像那年出租屋里她每次做完那种事之后穿衣服的时候——那种慢。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格一格的,每一格都能让人看清那手是怎么动的,那衣服是怎么穿上的。
她先穿那文胸。
那文胸在地上,扔在那堆雪白的狐皮旁边。她弯下腰去捡。那弯腰的动作——那腰弯下去,那臀翘起来,翘得那两瓣肉之间的沟更深了,深得像一道山谷。那沟里还湿着,亮着,是那胖子的东西,是她自己的东西,混在一起,分不清。那沟底那粉红色的地方在那光里一闪一闪的,像在说话。
她捡起那文胸。
直起腰。
那文胸在她手里,黑黑的,薄薄的,上面还有她的汗,亮亮的。她把那文胸举起来,对着那光看了看。那眼睛里的光——是嫌弃?是厌恶?还是那种“这玩意儿脏了”的无所谓?
她把那文胸扔了。
扔在地上。
没穿。
她捡起那狐皮外套。
那外套是雪白的,软软的,蓬蓬的,在那光里像一团云。她把那外套抖开,披在身上。那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膝盖。她把那外套拢在身前,用一只手捏着领口,遮住那胸前那两团肉。
那两团肉被遮住了。
可那腿遮不住。
那黑丝裹着的腿就那么露着,在那外套下面,从那雪白的狐毛边缘伸出来,白白的,长长的,亮亮的。那腿上还有那胖子的口水,有她自己流出来的东西,混在一起,在那黑丝下面一道一道的,像画上去的线。
她没穿那丁字裤。
那丁字裤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她也不找。就那么光着下面,只披着那件狐皮外套,穿着那黑丝。
她转过身。
面对着我。
面对着我这个角落。
面对着我这个戴着黑面具的人。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那笑里有话。
那话是——走吧。
她朝我走过来。
那脚步轻轻的,细细的,踩在石板地上,沙沙响。那狐皮外套在她身后一飘一飘的,像一朵云。那黑丝裹着的腿在那外套下面一闪一闪的,白白的,亮亮的。那腿一动,那大腿根部就露出来一点——那大腿根部,那光光的、白白的皮肤,那皮肤上还沾着东西,亮亮的,在那光里一闪。
她走到我面前。
站在我面前。
站在那两只手就能抱住的距离里。
她低下头。
望着我。
望着我这个戴着黑面具的人。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还沾着那胖子的口水,沾着她自己嘴里流出来的东西,黏黏的。那手伸过来,碰到我的脸,碰到那黑面具的边缘。
她摸着那面具。
轻轻地。
慢慢地。
然后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那一个字像一团火。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那嘴角的笑,那脸上淌着的汗,那嘴角那粉粉的新肉。
我张了张嘴。
那话从喉咙里出来,哑哑的。
“妈——”她笑了。
那笑从那眼睛里溢出来,从那亮亮的光里溢出来。
“傻孩子——”她说,“走吧。”然后她转过身。
朝那门口走去。
我跟在她身后。
那脚步轻轻的,细细的,踩在石板地上,沙沙响。她走在前面的影子在那昏黄的光里一晃一晃的,那狐皮外套在她身后一飘一飘的,像一朵云。那黑丝裹着的腿在那外套下面一闪一闪的,白白的,亮亮的。
我推开门。
那门吱呀一声开了。
外面是院子。
那院子里阳光很烈。白花花的,照得人眼睛疼。
母亲走出去。
走进那阳光里。
那阳光打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都照亮了。那雪白的狐皮外套在那阳光里更白了,白得刺眼,白得像一团火。那黑丝裹着的腿在那阳光里更亮了,亮得像涂了一层油。那腿上那一道一道的东西在那阳光里清清楚楚的,像画上去的线。
她站在那阳光里。
回过头。
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走啊。”她说。
我走出去。
走进那阳光里。
那阳光打在我身上,热热的,烫烫的,像要把人烤化。那灰扑扑的仆人的衣服在那阳光里更灰了,灰得像一团泥。那黑面具在那阳光里更黑了,黑得像一块炭。
我走到她身边。
站在她身边。
她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笑更深了。
然后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还沾着那东西,黏黏的,在那阳光里亮着。
她的手伸过来。
握住我的手。
那手热热的,软软的,滑滑的。
她握着我的手。
握得紧紧的。
然后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走吧。”她说,“回家。”那两个字像两团火。
我们走。
走出那院子,走过那一进一进的院子,走过那一重一重的门。那副使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跟在后面,那老鼠尾巴似的胡子一翘一翘的,那脸上的表情——是笑,是那种“钱真好赚”的笑,也是那种“你们快走吧”的急。
他送我们到门口。
那衙门的大门。
门口那两个兵还站着,还握着那长枪,那脸上的表情——是木的,是那种“什么都没看见”的木。
我们走出去。
走出那大门。
走进那街道。
那街道上人很多。有穿袍子的,有穿皮袄的,有汉人,有藏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走来走去的,走来走去的,各忙各的。
没人注意我们。
一个披着狐皮外套的女人,一个穿着灰扑扑衣服的男人,手牵着手,走在街上,谁会在意?
可我在意。
我在意她走路的姿态。
那姿态还是一扭一扭的,一摇一摆的,和刚才在那屋里跳的时候一样。可那扭里,那摇里,多了什么——多了累?多了软?还是多了那种做完事之后的慵懒?
那狐皮外套在她身后一飘一飘的,飘得那雪白的狐毛在那阳光里一闪一闪的。那外套下面,那黑丝裹着的腿一前一后地动着,那腿上的东西在那阳光里干了,干了之后在那黑丝上留下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像盐碱地上的霜。
那腿一动,那大腿根部就露出来一点——那大腿根部,那光光的、白白的皮肤,那皮肤上还沾着东西,干了之后也变成白印子,一道一道的,像画上去的花纹。
有人看。
有男人看。
那些男人的眼睛从四面八方射过来,射在她身上,射在那黑丝裹着的腿上,射在那大腿根部一闪一闪的白肉上。那眼睛里有什么?有那种“这女人真骚”的光,有那种“她刚干完什么”的猜,还有那种馋,那种想吃又吃不到的馋。
她不在乎。
她只是走。
一扭一扭的,一摇一摆的,手握着我的手,握得紧紧的。
我握着她的手。
握着那白白的、软软的、滑滑的手。
那手上有汗,有那胖子的口水,有她自己的东西,混在一起,黏黏的,干了之后变得涩涩的,可那涩里还有滑,还有那种说不清的东西。
我们走过那些街道,走过那些帐篷,走过那些站着的人。
走过那卖酥油茶的摊子,那卖糌粑的铺子,那拴着马的木桩。
走过那来来往往的人。
走到那狼部的营地。
那营地就在前面。那些帐篷,那些黑黑的、用牦牛毛织成的帐篷,在那阳光下黑黑的,像一堆一堆的蘑菇。那帐篷前面有人——有我们狼部的人,有站岗的,有走来走去的。
他们看见我们了。
看见母亲披着那狐皮外套,光着两条黑丝裹着的腿,手握着我的手,走回来。
他们的眼睛——那眼睛里有东西。
那东西是什么?是那种“夫人回来了”的平常?还是那种“夫人怎么这样回来”的意外?还是那种“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的那种躲闪?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母亲不在乎。
她只是走。
走进那营地。
走进那些帐篷中间。
走到我们的帐篷前面。
那帐篷还是那样。那帘子还是垂着,那帘子上还是那幅画——那幅画着狼的画,那狼的眼睛还是那样,凶凶的,像活的一样。
她停下来。
站在那帐篷前面。
站在那阳光下。
她松开我的手。
转过身。
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儿——”她说。
我望着她。
“妈——”她笑了。
那笑从那眼睛里溢出来,从那亮亮的光里溢出来。
然后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那东西干了之后变成白白的粉末,在那手心里一道一道的。
她的手伸过来。
碰到我的脸。
碰到那黑面具的边缘。
她摸着那面具。
轻轻地。
慢慢地。
然后她把那面具摘下来。
那面具从我脸上离开。那阳光打在我脸上,热热的,烫烫的,刺得我眼睛疼。我眯着眼,望着她。
她望着我。
望着我的脸。
那眼睛里的光——那光里有心疼?有怜爱?还是有那种“孩子受苦了”的那种疼?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傻孩子——”她说,“跟妈进去。”然后她掀开那帘子。
走进去。
我跟在她身后。
走进去。
那帐篷里很暗。从那白花花的阳光里走进来,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那帘子在身后落下来,把那阳光挡在外面。只能看见那昏昏的暗影,那暗影里有一点光——是那盏酥油灯,还亮着,还亮着一点昏黄的光。
我站在那儿。
站在那暗影里。
眼睛慢慢适应了那暗。
能看见了。
看见那帐篷里的东西——那铺在地上的皮毛,那摆着的箱子,那挂着的衣服,那一切。
看见母亲。
她站在那暗影里。
站在那昏黄的光里。
站在我面前。
那狐皮外套还披在身上,还拢在身前,还捏着那领口。那雪白的狐毛在那昏黄的光里变成淡黄色,软软的,蓬蓬的,像一团云。那黑丝裹着的腿在那光里还是那么亮,亮得像涂了一层油。
她站在那儿。
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话。
那话是——她松开手。
那捏着领口的手松开。
那狐皮外套散开。
从她肩上滑下来。
滑下来。
滑落在地上。
落在那皮毛上。
雪白的一团,像一堆云。
她站在那儿。
站在那昏黄的光里。
站在我面前。
一丝不挂。
那身体——那身体在那光里泛着光。那皮肤白白的,滑滑的,上面全是汗,亮亮的。那汗从额头淌下来,淌过眉骨,淌过眼睛,淌过脸颊,淌到下巴,一滴一滴的,像眼泪。可那不是眼泪。那是汗。是刚才做那事做出来的汗。
那汗淌过那脖子,淌过那锁骨,淌到那胸前——那胸前那两团巨乳。那两团肉在那光里白得像雪,软得像棉花,圆得像碗,上面全是汗,亮亮的。那两团肉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的。一起——那肉更鼓了,那乳尖更高了。一伏——那肉软一点,那乳尖低一点。那起起伏伏的,像两座会动的山。那左乳上的朱砂痣在那片白里红得像一滴血,在那光里一跳一跳的,像一颗会动的小豆子。
那汗淌过那胸,淌过那肚子——那肚子平平的,滑滑的,上面也有汗,亮亮的。那肚脐眼在那光里一个小小的坑,那坑里也积着汗,亮亮的。
那汗淌过那腰——那腰细得不像话,细得像一只手就能握住。那腰上还有那胖子手抓出来的红印,一道一道的,在那白白的皮肤上很明显。那红印像画上去的线,一道一道的,在那汗里亮着。
那汗淌过那胯——那胯间,那两腿之间。那地方——那地方湿湿的,亮亮的,毛都贴在皮肤上,一绺一绺的。那毛是黑的,在那白白的皮肤上很明显。那毛下面那地方——那地方还张着,还红着,还肿着,还有东西从那里面流出来,白白的,黏黏的,顺着那大腿内侧往下淌,淌过那大腿,淌过那膝盖,淌到那小腿,淌到那脚踝,淌到那脚上。
那大腿上全是那东西。干了之后变成白白的印子,一道一道的,像画上去的花纹。那黑丝裹着的腿上也有,在那黑丝下面,那白印子一道一道的,像盐碱地上的霜。
她站在那儿。
站在那光里。
站在我面前。
她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那一个字像一团火。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那嘴角的笑,那脸上淌着的汗,那嘴角那粉粉的新肉,那胸前那两团巨乳,那左乳上的朱砂痣,那肚子,那腰,那胯间那湿湿的、亮亮的、还在流着东西的地方。
我张了张嘴。
那话从喉咙里出来,哑哑的。
“妈——”她笑了。
那笑从那眼睛里溢出来,从那亮亮的光里溢出来。
然后她走过来。
站在我面前。
站在那两只手就能抱住的距离里。
她抬起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那东西干了之后变成白白的粉末,在那手心里一道一道的。
她的手伸过来。
碰到我的脸。
碰到我的脸颊。
她摸着我的脸。
轻轻地。
慢慢地。
那手凉凉的,滑滑的,带着那粉末的涩。
她摸着我的脸。
摸着我的眉毛,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唇。
她摸着我的嘴唇。
那手指按在我嘴唇上,一按一按的,像在弹琴。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她说,“妈回来了。”那五个字像五根针。
扎在我心上。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
那眼睛里有什么?
那光里有什么?
有累?
有软?
有那种做完事之后的慵懒?
还是有那种“妈没事”的那种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那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热热的,烫烫的,淌过脸颊,淌到她的手上。
她的手碰到那眼泪。
那眼泪在她手心里,热热的,湿湿的。
她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那笑从那嘴角溢出来,从那粉粉的新肉旁边溢出来。
“傻孩子——”她说,“哭什么?”我张了张嘴。
那话从喉咙里出来,哑哑的,带着哭腔。
“妈——我——我担心——”她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软了。
软得像水。
她伸出手。
那两只手捧住我的脸。
捧得紧紧的。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可那软里还有别的——是那种“妈懂”的那种软。
“傻孩子——”她说,“妈干这个干了几十年了。没事的。”她顿了顿。
那眼睛里的光更深了。
“再说了——”她说,那声音压低了,低得像耳语,“妈不是给你表演了吗?”那七个字像七团火。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那嘴角的笑。
那笑里有话。
那话是——好看吗?
我的脸红了。
那红从脖子根往上涌,涌到脸上,热热的,烫烫的。
她看见我脸红。
那笑更深了。
她松开手。
转过身。
朝那箱子走去。
那箱子是黑黑的,旧旧的,放在帐篷的一角。她走过去,那背影——那背光滑的,白的,上面全是汗,亮亮的。那汗从背上淌下来,淌过那腰,淌过那臀,淌过那大腿,淌到那小腿。那臀上还有那胖子手抓出来的红印,一道一道的,在那白白的皮肤上很明显。那两瓣臀肉随着她的步子一颤一颤的,一颤一颤的,像两团在风里的果冻。那两腿之间,那东西还在往下淌,顺着那大腿内侧淌下来,在那腿上留下一道亮亮的水痕。
她走到那箱子前。
弯下腰。
打开那箱子。
那弯腰的动作——那腰弯下去,那臀翘起来,翘得那两瓣肉之间的沟更深了,深得像一道山谷。那沟里还湿着,亮着,是那胖子的东西,是她自己的东西,混在一起,分不清。那沟底那粉红色的地方在那光里一闪一闪的,像在说话。
她在箱子里翻着什么。
翻了一会儿。
直起腰。
转过身。
手里拿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信函。黄黄的,用红绸子系着,上面盖着朱红的大印——那印很大,很圆,在那黄绫子上像一朵开得正盛的花。
一样是文书。厚厚的,折着的,也是黄的,也盖着印。
那是刚才在公孙富山那里拿的东西。
那两样东西。
她拿着它们。
走回来。
走到我面前。
站在我面前。
站在那两只手就能抱住的距离里。
她把那两样东西举起来。
在我眼前晃了晃。
那两样东西在那昏黄的光里一晃,一晃的,那红绸子一闪一闪的,像一团火。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她说,“你看。”我望着那两样东西。
望着那黄黄的绫子,那朱红的大印。
她笑了。
那笑从那嘴角溢出来,从那粉粉的新肉旁边溢出来。
“这是给你的。”她说,“狼部镇守使的任命书。盖好印子的。”她把那信函塞进我手里。
那信函沉沉的,滑滑的,那红绸子在我手心里凉凉的。
她又举起那文书。
“这是贸易许可书。”她说,“有了这个,狼部就能和大夏做生意了。卖我们的皮子,卖我们的盐,买我们要的东西。朝廷不收税。三年。”三年免税。
那五个字像五块金子。
她把那文书也塞进我手里。
那文书厚厚的,沉沉的,那黄绫子在我手心里滑滑的。
我捧着那两样东西。
捧着它们。
手在抖。
在抖。
在抖。
她望着我。
望着我那抖着的手。
那眼睛里的光软了。
软得像水。
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那东西干了之后变成白白的粉末,在那手心里一道一道的。
她的手握住我的手。
握住我那捧着文书的手。
握得紧紧的。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她说,“妈给你挣来的。”那七个字像七根针。
扎在我心上。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
那眼睛里有什么?
有累?
有软?
有那种“妈值不值”的那种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那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热热的,烫烫的,淌过脸颊,滴在那文书上,一滴,两滴,三滴。那眼泪在那黄绫子上晕开,把那朱红的大印晕得模糊了一点。
她望着那眼泪。
望着那晕开的印子。
她笑了。
那笑从那眼睛里溢出来,从那亮亮的光里溢出来。
“傻孩子——”她说,“哭什么?这是好事。”她顿了顿。
那眼睛里的光更深了。
“还有一样东西。”她说。
她松开手。
转过身。
又朝那箱子走去。
又弯下腰。
又在箱子里翻。
又直起腰。
转过身。
手里拿着另一样东西。
那东西是——一张纸。
一张白白的纸。
折着的。
四四方方的。
她拿着它。
走回来。
走到我面前。
站在我面前。
她把那纸举起来。
在我眼前晃了晃。
那纸在那昏黄的光里白白的,像一片雪。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她说,“你看这个。”我望着那纸。
那纸白白的,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什么?”我问。
她笑了。
那笑从那嘴角溢出来,从那粉粉的新肉旁边溢出来。
她打开那纸。
那纸折着,一层一层的。她一层一层地打开,打开,打开。
那纸打开了。
是一份文书。
上面写着字。
那字是汉文,工工整整的,像印上去的。
我望着那字。
那字一个一个地跳进眼睛里——“兹有……”“狼部……”“镇守使……”“之母……”“……”我望着那字。
望着望着。
那字在我眼前模糊了。
因为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那是——那是进入内地的通行证。
给母亲的。
给她的。
有了这个,她就能跟我一起进内地了。就能离开这高原,离开这苦寒的地方,去那温暖的、富庶的、有花有草的内地了。
她望着我。
望着我那流着的眼泪。
那眼睛里的光软得像水。
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那东西干了之后变成白白的粉末,在那手心里一道一道的。
她的手伸过来。
擦我的眼泪。
那手指凉凉的,滑滑的,带着那粉末的涩。她擦着,擦着,擦着我脸上的眼泪,擦得那眼泪在她手心里,湿湿的,热热的。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傻孩子——”她说,“哭什么?妈跟你一起走。”那七个字像七团火。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
那眼睛里有什么?
有笑。
有那种“妈高兴”的那种笑。
我张开嘴。
想说什么。
可说不出来。
只是哭。
只是流眼泪。
像个孩子。
像个几岁的孩子。
她望着我那样。
那眼睛里的笑更深了。
可那深里还有别的——是那种“妈懂”的那种软。
她松开手。
转过身。
又朝那箱子走去。
这一次,她没弯腰。
只是站在那箱子前。
从箱子上面拿起另一样东西。
那东西是——一张纸。
也是白白的。
也是折着的。
也是四四方方的。
她拿着它。
走回来。
走到我面前。
站在我面前。
她把那纸举起来。
在我眼前晃了晃。
那纸在那昏黄的光里白白的,像一片雪。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她说,“还有一样。”我望着那纸。
那纸白白的,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什么?”我问。
她笑了。
那笑从那嘴角溢出来,从那粉粉的新肉旁边溢出来。
可那笑里,有什么不一样。
是那种——是那种“妈有点不好意思”的那种笑?
她打开那纸。
那纸折着,一层一层的。她一层一层地打开,打开,打开。
那纸打开了。
也是一份文书。
上面也写着字。
那字也是汉文,工工整整的,像印上去的。
我望着那字。
那字一个一个地跳进眼睛里——“婚书……”“狼部镇守使……”“之母……”“与……”“狼部镇守使……”“……”我望着那字。
望着望着。
那字在我眼前停了。
停了。
不动了。
那是——那是婚书。
母亲和我的婚书。
我抬起头。
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
那眼睛里有什么?
有笑。
有那种“妈有点不好意思”的那种笑。
还有别的——还有那种“妈愿意”的那种光。
她望着我。
望着我那愣住的脸。
那笑更深了。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可那软里还有别的——是那种“傻孩子”的那种软。
“儿——”她说,“咱们还没办婚礼呢。可凭证,有了。”她把那婚书塞进我手里。
那婚书轻轻的,薄薄的,在我手心里,和那任命书,和那贸易许可书,和那通行证,放在一起。
我捧着那四样东西。
捧着它们。
手在抖。
在抖。
在抖。
我望着它们。
望着那任命书,那贸易许可书,那通行证,那婚书。
那四样东西在那昏黄的光里,在那酥油灯的光里,在那暗影里,亮亮的,像四团火。
我抬起头。
望着母亲。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
那眼睛里有什么?
有笑。
有那种“妈高兴”的那种笑。
还有别的——有那种“妈是你的”的那种光。
我张开嘴。
那话从喉咙里出来,哑哑的。
“妈——”她笑了。
那笑从那眼睛里溢出来,从那亮亮的光里溢出来。
她走过来。
站在我面前。
站在那两只手就能抱住的距离里。
她抬起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上面那东西干了之后变成白白的粉末,在那手心里一道一道的。
她的手伸过来。
捧住我的脸。
捧得紧紧的。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她说,“妈是你的人了。”那六个字像六根针。
扎在我心上。
可那不是疼。
那是别的。
那是——那是说不清的东西。
我望着她。
望着她那亮亮的眼睛,那嘴角的笑,那脸上淌着的汗,那嘴角那粉粉的新肉,那胸前那两团巨乳,那左乳上的朱砂痣,那肚子,那腰,那胯间那湿湿的、亮亮的、还在流着东西的地方。
我望着她。
望着我的女人。
望着我的妈。
我的眼泪又流下来了。
可那眼泪里,有笑。
她看见我那眼泪里的笑。
那眼睛里的光更深了。
她松开手。
转过身。
走到那堆皮毛旁边。
那皮毛厚厚的,软软的,铺在地上,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她站在那皮毛旁边。
转过身。
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软软的。
她伸着手。
望着我。
那眼睛里有话。
那话是——来。
我走过去。
走到她面前。
站在她面前。
站在那皮毛旁边。
她望着我。
望着我的眼睛。
然后她笑了。
那笑从那嘴角溢出来,从那粉粉的新肉旁边溢出来。
她伸出手。
开始解我的衣服。
那动作很慢。
慢得像那年出租屋里她第一次给我脱的时候——那种慢。
她解着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解。那衣服是灰扑扑的,是那仆人的衣服,小得紧紧绷在身上。她解着,解着,把那衣服解开,脱下来,扔在地上。
我站在她面前。
光着上身。
她望着我。
望着我的胸膛,我的肩膀,我的胳膊。
那眼睛里的光——是那种“我儿子真壮”的那种光。
她的手伸过来。
摸着我的胸膛。
那手凉凉的,滑滑的,带着那粉末的涩。她摸着我的胸膛,摸着那结实的肌肉,摸着那跳动的心。
她摸着。
摸着。
然后她低下头。
把脸贴在我胸膛上。
贴在那跳动的地方。
她的头发散着,那高高的发髻早就歪了,那绿松石的簪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那头发散下来,黑黑的,长长的,披在肩上,披在背上,披在那白白的皮肤上。
她把脸贴在我胸膛上。
贴得紧紧的。
她开口。
那声音闷闷的,从她嘴里出来,从她贴着我胸膛的嘴里出来。
“儿——”她说,“妈累了。”那三个字像三团火。
我低下头。
望着她那散着的头发,那白白的脖子,那背上那一道一道的汗,那腰上那红红的印子。
我抬起手。
那手抖抖的。
我的手放在她头上。
放在她那散着的头发上。
那头发滑滑的,软软的,带着汗,带着那晚香玉的残香。
我摸着她的头发。
轻轻地。
慢慢地。
她没动。
就那么贴着我。
贴了很久。
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
望着我。
那眼睛亮亮的。
那亮里有笑。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儿——”她说,“陪妈躺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
躺在那皮毛上。
躺在那厚厚的、软软的皮毛上。
她躺着。
那身体在那昏黄的光里泛着光。那皮肤白白的,滑滑的,上面全是汗,亮亮的。那胸前那两团巨乳往两边摊开,软软的,像两座摊开的小山。那左乳上的朱砂痣在那片白里红得像一滴血,在那光里一跳一跳的。那肚子平平的,滑滑的,那肚脐眼一个小小的坑。那胯间那地方还湿着,亮着,那毛一绺一绺的,贴在皮肤上。
她躺着。
望着我。
那眼睛里有话。
那话是——来。
我躺下去。
躺在她身边。
躺在那厚厚的、软软的皮毛上。
我侧过身。
望着她。
望着她的脸。
她也侧过身。
望着我。
望着我的脸。
我们就这样望着。
望着。
望着。
在这昏黄的帐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