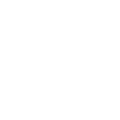22、
那晚之后,我和程述言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
一种互相躲避的默契。
在宿舍里,只要他在公共区域,我就绝对不会从我的床上下来。只要我坐在书桌前,他进门后就会目不斜视地直接爬上他的床。我们两个人就像是磁铁的同极,永远在互相排斥。如果必须要在宿舍里走动,我们的行动轨迹也会像经过精密计算一样,完美地错开,绝不产生任何交集。
宿舍的其他人都没发现这种异常。她们只当我还在为那段子虚乌有的“恋情”而伤感,默契地不再提起任何和感情有关的话题。而程述言,也恢复了他那“高冷社恐”的常态。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知道多久。五天?十天?我记不清了。
我的情绪,从最开始的崩溃和绝望,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钝刀子割肉般的煎熬。
我恨他,恨他看到了我不堪的一面。
我怕他,怕他会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我躲着他,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他。
可是……我又感激他。
是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不动声色地,递给了我一个台阶。他编造的那个谎言,是我现在还能留在这个学校的唯一理由。
我必须得去道谢。
于情于理,都必须。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慢慢发芽。但每当我鼓起一点点勇气,准备行动的时候,中午那个不堪的画面,就会立刻跳出来,把我所有的勇气都烧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我在“应该去道谢”和“我没脸见他”之间,反复挣扎,备受煎熬,感觉自己都快精神分裂了。
直到那天傍晚。
我抱着几本书从图书馆出来,准备回宿舍。路过操场时,我的脚步鬼使神差地停住了。
在操场边上的长椅上,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程述言。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服,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远处正在进行足球比赛的人群。夕阳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背影看起来……有些孤独。
我的心,莫名地被触动了一下。
就是现在。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犹豫和纠结。
他只有一个人。没有宿舍里那些“观众”,这是最好的时机。
我把书紧紧地抱在怀里,转身走向操场边上的小卖部。我的手心在出汗,心脏砰砰直跳。我对着货架发了半天呆,最后拿了两瓶冰镇的矿泉水。
付钱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我捏着冰凉的瓶身,给自己做着最后的心理建设。
“李依依,你可以的!不就是说声谢谢吗?三秒钟就搞定!说完就跑!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深吸一口气,像一个即将奔赴刑场的死囚,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朝着那条长椅走去。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感官都变得异常敏锐。我能听到远处踢球的呼喊声,能闻到空气中青草的味道,能感觉到晚风吹过我脸颊时,那滚烫的温度。
终于,我走到了他的身边。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用一种极其僵硬的姿态,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我们之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他似乎感觉到了身边的动静,转过头来。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平静无波,像一潭深水。宿舍里昏暗的灯光不同,在夕阳下,我能清晰地看到他干净的眉眼,挺直的鼻梁,和他那因为有些意外而微微抿起的嘴唇。
然后,他开口了。
“怎么了?”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像一把重锤,瞬间击碎了我刚刚才用胶水勉强粘合起来的全部勇气。
我所有的信心,在这一刻,瞬间瓦解。
我感觉自己的脸颊“轰”的一下就烧了起来,温度高到仿佛能把空气都点燃。我准备好的一百句开场白,什么“学长谢谢你那天帮我解围”,什么“那天的事我很抱歉”,此刻全都变成了无法解读的乱码。
我猛地一下低下头,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鞋尖,感觉自己连呼吸都做不到了。
完蛋了。
又来了。
在他面前,我好像永远都是这副上不了台面的、丢人现眼的怂样。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最后,只能用一种近乎痉挛的动作,把手里那瓶冰凉的矿泉水,往他那里递了递。
空气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远处球场上的欢呼声,此刻听起来是那么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