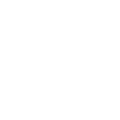不知过了多久,仿佛从无尽的海底挣扎着浮出水面,方君的意识一点点回归。头脑像是被灌满了沉重的铅块,昏沉而滞涩,四肢百骸更是酸软乏力,连最简单的抬动手指都显得异常艰难。他发现自己穿着一身从未见过的丝质睡衣,面料柔软得如同第二层皮肤,正躺在一张宽阔得有些过分、异常柔软的大床上。厚重的窗帘严丝合缝,挡住了外界的全部光线,房间里一片死寂,只有他自己略显急促的呼吸声。窗外是无边的漆黑,分辨不清是深夜还是黎明前最沉郁的时分。
一种莫名的空虚感和隐约的不安驱使着他挣扎起身。脚下是冰凉而光滑的木地板,他蹑手蹑脚地推开卧室门。幽深的走廊空无一人,只有墙壁上几盏壁灯散发着昏黄黯淡的光晕,将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形同鬼魅。就在这片沉寂之中,走廊对面的一扇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种幽暗的、仿佛具有生命般脉动着的深红色光芒,像一颗在黑暗中跳动的心脏,散发着不祥而诱惑的吸引力。
鬼使神差地,他被那光芒攫住了,脚步不受控制地挪了过去,轻轻推开了那扇门。
刹那间,仿佛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是一间布置得极其奢靡,甚至到了颓废程度的卧室。深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沉重地垂落,隔绝了外界;深红色的床幔如同舞台帷幕般从天花板上倾泻而下,笼罩着那张巨大得惊人的床榻;深红色的床单与被褥凌乱地铺陈着,一切都浸润在一种暧昧、危险、令人心跳加速的深红基调之中。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浓烈而奇异的香气,混合着昂贵的香水、女性肉体的温热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欲蒸腾后的甜腥气息。
罂夫人就斜倚在那张仿佛能吞噬一切的大床中央。她只穿着一件用料极其节省、几乎是透明的深红色薄纱睡裙,丝滑的布料紧贴着她丰腴起伏的胴体,勾勒出惊心动魄、成熟欲滴的曲线。睡裙下摆短得只堪遮住腿根,那双修长浑圆的玉腿肆无忌惮地交叠着,包裹在某种带有细腻暗纹的、泛着哑光的黑色丝袜之中,一直延伸至大腿根部,袜口边缘勒出一圈微微陷入软肉的迷人痕迹。
“方君,你醒了。”罂夫人的声音带着一丝事后的慵懒和沙哑,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酣畅的欢愉,眼神迷离而湿润,直勾勾地望过来,“过来。”方君的心脏猛地一缩,随即疯狂地擂动起来。他咽了口发干的唾沫,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咕噜”声。怀揣着巨大的恐惧、无法抑制的好奇,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清晰察觉、却已在身体深处悄然燃起的期待,他像个提线木偶般,一步步挪向那张大床。脸上火烧火燎,视线不由自主地低垂,不敢与那双仿佛能吸走人灵魂的眸子对视,目光最终飘忽着落在地毯上,却又被那双包裹在黑丝中、微微弓起的玉足所牢牢吸引。那足型完美,脚踝纤细,足弓的弧度优雅诱人,透过薄薄的丝袜,能清晰地看到微微凸起的踝骨和淡青色的血管脉络,十个脚趾涂着与睡裙同色的深红蔻丹,宛如十颗熟透的浆果,在黑色的束缚中不安分地蜷缩着,充满了无声的挑逗。
“我的丈夫去世得早,只留下这偌大的家业,和我那不懂事的女儿……”罂夫人轻声叹息,语气里充满了幽怨与深入骨髓的寂寞,她微微调整了一下姿势,让睡裙的领口滑落得更低,露出一片雪白滑腻的胸脯,“有时候,夜深人静,真是感到……无比的冰冷和孤独呢。”方君张了张嘴,喉咙却干涩得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声音,正不知该如何回应这直白的倾诉,一只微凉而柔软的手突然如灵蛇般探出,精准地抓住了他的手腕。那看似纤弱的手掌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容抗拒地将他猛地一拽!
“夫人!”天旋地转间,方君惊呼一声,整个人已被一股巨力拉扯着,摔进了那张柔软得如同沼泽般的大床上。羽绒床垫深深地陷了下去,将他包裹。他还未及挣扎起身,罂夫人已经轻笑着翻身压上,她的动作熟练而迅捷,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
“别紧张,小家伙……”她呵气如兰,温热的气息喷在他的耳廓,一只手轻易地制住他无力的反抗,另一只手则灵巧地探入他的睡裤边缘,向下一剥!
微凉的空气瞬间侵袭了他赤裸的下体,让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那根尚且处于半休眠状态的男性象征,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露和极度紧张的情绪,微微颤抖着,显露出一种无助的青涩。
罂夫人俯下身,鲜艳欲滴的红唇勾勒出一抹玩味的弧度。她伸出舌尖,那舌尖小巧而灵活,带着湿漉漉的光泽,如同品尝什么稀世珍馐一般,精准无比地、轻轻点在了他那因紧张而紧缩的马眼之上。
“唔——!”当那一点极致湿润、温软、带着轻微摩擦感的触感抵住最敏感核心的瞬间,一股完全无法抗拒的、如同电流般爆炸性的快感,从尾椎骨沿着脊柱疯狂窜升,直冲方君的头顶!他双眼猛地瞪大,瞳孔涣散,大脑一片空白。双腿像被强直拉伸般骤然绷紧,腰肢完全不受控制地向上剧烈挺动,一股积蓄已久的白浊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猛烈地喷射而出,尽数溅射在了罂夫人近在咫尺的脸颊、唇角和她那雪白的颈窝之上。
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淡淡的、属于年轻男性的腥膻气息。
短暂的极致空白过后,是铺天盖地的羞耻与慌乱。
“对…对不起!夫人!我……我不是故意的!”方君羞愧得无地自容,脸颊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手忙脚乱地想找东西为她擦拭,却发现自己浑身瘫软,动弹不得。
罂夫人的脸上极快地闪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失望,那神情如同流星般转瞬即逝,随即被一种更深沉、更玩味的笑容所取代。她非但没有动怒,反而伸出舌头,仔细地、甚至带着一丝明显享受意味地,将溅落在自己唇角、脸颊肌肤上的粘稠汁水,一点点、慢条斯理地舔舐干净。那动作优雅而淫靡,仿佛在品尝什么琼浆玉液。
“还真是……青涩得可爱呢。”她的声音带着饱含情欲的沙哑,指尖轻轻抹过颈窝处的白浊,然后放入口中吮吸干净。
随后,在方君依旧沉浸在巨大的羞耻和茫然中时,她变戏法般再次拿出了那个眼熟的粉色药剂瓶。冰凉的瓶口对准他那刚刚释放过、正处于不应期而疲软萎缩的肉棒,轻轻按压喷头,“嗤嗤”两声,带着甜腻香气的雾状液体均匀地覆盖了上去。
奇异的、如同火焰灼烧般的热流瞬间从皮肤表面渗透,沿着神经末梢急速蔓延!方才还萎靡不振的肉棒,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违背生理常识地重新充血、膨胀、勃起!不过几个呼吸间,它已变得比之前更加粗壮、坚挺,直愣愣地矗立在双腿之间,血管虬结,散发出滚烫的温度和惊人的生命力,仿佛有独立的意志在驱使。
“看来,仅仅是这样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呢。”罂夫人轻笑着,声音如同包裹着蜜糖的毒药,“需要更多的……‘锻炼’才行啊,我亲爱的方君。”她说着,优雅地抬起那双一直被方君偷偷注视的、包裹在顶级黑色丝袜中的玉足。柔软的脚掌带着温热的体温,轻轻贴上了他勃起的柱身。先是足弓最柔软的部位,如同情人的抚摸般,从上至下,缓慢而充满挑逗地摩擦、按压。丝袜细腻滑腻的触感,与足底肌肤特有的温热和微妙纹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直击灵魂的奇特刺激。
方君倒抽一口冷气,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呜咽。那灵活的脚趾开始加入这场淫戏,它们如同拥有独立生命的小蛇,时而用趾腹夹住敏感的龟头边缘轻轻捻动,时而并拢在一起,紧紧包裹住怒张的蘑菇头,施加恰到好处的压力,时而又用趾缝夹住系带所在的脆弱部位,带来一阵阵令人头皮发麻的酸麻感。
视觉上,那双被黑色丝袜严密包裹的玉足,在他古铜色的、青筋暴露的昂扬肉棒上滑动、揉弄,黑白分明,色彩对比强烈到刺眼,充满了堕落的视觉冲击力。嗅觉里,是空气中尚未散尽的、属于他自己的精液气息,混合着罂夫人身上浓郁的异香,以及丝袜长时间包裹后微微蒸腾出的、带着一点皮革和女性荷尔蒙的复杂味道。触觉上,丝滑、温热、压迫、摩擦……各种感觉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快感之网,将他牢牢困在其中。
在这高超而富有技巧的足交侍弄下,方君本就敏感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密集而强烈的刺激。他的喘息变得粗重而破碎,腰肢开始失控地随着那双玉足的动作而微微挺动,寻求更深的接触。快感如同不断上涨的潮水,迅速累积,冲向那个临界点。
“啊……夫人……不行了……要……要去了……”他断断续续地哀求着,眼神迷离。
罂夫人却仿佛没有听到,足上的动作反而加快了几分,脚趾更加用力地揉按着龟头最敏感的顶端和马眼。
“射出来。”她命令道,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魔力。
“嗬——!”方君发出一声如同濒死般的悠长抽气,身体像一张拉满的弓骤然松开,腰部剧烈地向上痉挛挺动,一股比第一次更加浓稠、量也更多的白浊,猛烈地喷射而出。大部分射在了罂夫人继续动作的黑丝玉足上,粘稠的液体玷污了那光滑的黑色表面,顺着足弓和脚趾滴滴答答地滑落,在白炽灯下反射出淫靡的光泽。还有几股甚至溅到了她深红色的睡裙和下摆边缘,黑白红三色交织,构成一幅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罂夫人似乎对此早有预料,甚至乐在其中。她再次拿起那仿佛取之不尽的粉色药剂,对着他那可怜兮兮、刚刚剧烈喷射过却依旧在药力作用下顽强保持着硬度的肉棒,毫不留情地连喷了两下。
“呃啊——!”更加炽烈的灼烧感传来,方君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那根肉棒仿佛被注入了一种狂躁的生命力,胀大了一圈,颜色变得深红,不受控制地跳动着,显示出一种被过度榨取后的狰狞状态。
然后,她跨坐到他的大腿根部,用自己柔软湿滑的腿心轻轻磨蹭着他的皮肤。在他因这接连不断的、远超承受极限的强烈刺激而眼神涣散、意识模糊之际,罂夫人不知从何处,取出了一个巨大得令人咋舌、尺寸远超常人的肉色塑胶阳具,以及一个外形设计极其逼真、入口处模仿着女性阴唇褶皱的飞机杯。
“看明白了吗,方君?”她舔了舔自己愈发红艳的嘴唇,眼神迷醉地看着那根巨大的假阳具,然后伸出舌头,如同侍奉真正的男性一般,开始细致地、充满色情意味地舔弄那橡胶龟头,沿着柱身上的模拟血管纹理一路向下,再将其深深含入口中,模仿着深喉的动作,不断抽插,发出令人面红耳赤的“啧啧”水声。她含糊不清地说着,声音混合着唾液和情欲,“你还……远远满足不了我呢……还需要……再成长哦……”她将那个名为“飞机杯”的、内部构造极其复杂紧致的器具,熟练地套在方君那根被药力强行维持着勃起、敏感度却已达到极致的肉棒上。内部那无比紧致、布满无数细小颗粒和螺旋褶皱的触感,疯狂地模拟着女性最私密蜜穴的吮吸和蠕动,带来一阵阵强过一阵的、几乎要将他逼疯的极致快感。
同时,她一只手握着那根粗长骇人的假阳具,调整了一下角度,然后毫不犹豫地、狠狠地插进自己早已泥泞不堪、汁水淋漓的下身!
“啊……进来了……好满……”罂夫人发出一声混合着痛苦与极致欢愉的、拖长了音调的淫靡长吟,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开始疯狂地扭动腰肢,自主抽插起来。
方君眼睁睁看着那根粗长的、不属于他的物体,消失在罂夫人那神秘而诱人的腿心深处,听着她毫不掩饰的、高亢而放浪的呻吟与喘息,感受着自己肉棒被那“飞机杯”内壁剧烈收缩、吮吸和摩擦所带来的、如同浪潮般一波波涌来的灭顶快感……视觉与触觉的双重冲击将他推向了理智崩溃的边缘。
视觉与触觉的双重夹击,如同两股性质相反却同样狂暴的电流,在方君体内疯狂冲撞、撕扯。他眼睁睁看着罂夫人如何贪婪地吞吐那根巨大的异物,耳中充斥着她混合着痛苦与极致欢愉的呻吟,而自己最脆弱的部位,正被一个冰冷而精巧的器械无情地榨取、模仿着最极致的性爱体验。这种割裂感让他眩晕,羞耻心早已被碾碎,只剩下最原始的、被强行灌输和放大的生理反应。
“不…停下……求求你…”他的哀求微弱得如同蚊蚋,破碎在喉咙深处。身体却背叛了他的意志,在那飞机杯内部愈发剧烈的收缩和模拟蠕动下,腰肢如同上了发条般,不受控制地、痉挛性地向上挺动,迎合着那致命的吮吸。药力在血液里燃烧,让他的感官敏锐到可怕的程度,每一次摩擦都带来近乎疼痛的尖锐快感。
就在罂夫人握着那根巨大假阳具,动作越来越狂野,呻吟愈发高亢,即将攀上顶峰的前一刻——方君再也无法承受。
被那紧箍的飞机杯疯狂榨取,视觉与听觉又被罂夫人极度淫靡的姿态所冲击,那积累到顶点的快感如同决堤的洪水,猛地冲垮了他最后一丝理智的堤坝。他喉间发出一声短促而绝望的鸣咽,腰眼一麻,一股滚烫的白浊便在剧烈的痉挛中,尽数喷射进了飞机杯紧致的深处。
刹那间,他浑身力气仿佛被抽空,整个人如同烂泥般瘫软下去,深陷在柔软的被褥里,只剩下胸膛剧烈起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上昏暗的光量。那根刚刚释放过的肉棒,在药力的残余作用下,依旧可怜地、半硬地挺立着,上面还套着那个沾满了它自身分泌物的飞机杯。
罂夫人似乎被他的突然喷射所刺激,动作骤然停顿,随即发出一声更加满足的、拖长了音调的尖叫,身体剧烈地抽搐了几下,才像被抽去所有骨头般,软软地倒在了方君的身边,大口喘息着,脸上弥漫着一种饕足却又更深层次空虚的复杂神情。
短暂的寂静只持续了片刻。
罂夫人侧过身,指尖带着微凉的汗意,划过方君汗湿的胸膛。她的眼神迷离,却带着一种审视猎物般的玩味。
“这就……不行了吗?”她轻笑,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看来,仅仅是这样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呢。”说着,她优雅地、慢条斯理地开始动作。先是伸手,将那个套在方君身上的飞机杯取了下来,随手扔在一边,里面残留的粘稠液体在深红色床单上留下暖昧的痕迹。接着,她双手伸到腰间,勾住那薄如蝉翼的深红色睡裙边缘,轻轻向上一提,便将这件唯一的遮蔽物从头顶脱了下来,随意丢弃在地毯上。
现在,她全身赤裸地呈现在方君眼前。成熟的胴体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饱满的双乳随着呼吸微微起伏,顶端的蓓蕾因为之前的兴奋而坚挺着。她的腰肢纤细。小腹平坦,再往下,是那片神秘而湿润的幽谷。
然而,她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放在了自己的腿上。她微微弓起身,双手沿着大腿优美的曲线向下,勾住了那双黑色丝袜的袜边。随着她缓慢而充满暗示性的动作,丝袜被一点点卷下,露出底下更加白皙滑腻的肌肤。当丝袜被完全褪到脚踝,她抬起一只脚,用脚尖灵巧地挑着,将两只丝袜都踢到了一边。现在,她那双曾让方君心神摇曳的玉足,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空气中。脚型完美,脚趾如珍珠般圆润,依旧涂着深红色的蔻丹,在灯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泽。
罂夫人跪坐起来,俯身靠近方君。她抬起一只脚,那微温的、带着一丝奇特汗湿气息的脚掌,轻轻地、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抵住了方君的脸颊,将他的头微微压向一侧。
“闻到了吗?”她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这是我的味道……混合着你的……还有那药剂的芬芳……”方君被迫近距离地感受着那只玉足。一股复杂的气味涌入鼻腔——不仅仅是单纯的脚汗味,更混合了她身上浓郁的体香、之前情欲蒸腾后的甜腥,以及一丝丝药剂带来的甜腻。这气味并不难闻,反而带着一种极其堕落、令人头晕目眩的催情效果。他的脸颊瞬间滚烫,羞耻感再次淹没了他,可身体深处那被药物点燃的火苗,却不受控制地重新窜起。
紧接着,罂夫人用那只抵住他脸的脚向下滑去,脚掌再次覆盖在他那半软的肉棒上。同时,她另一只脚也加入进来。这一次,没有了丝袜的阻隔,足底肌肤那细腻的纹理、温热的触感、以及微微的湿意,带来了比之前更加直接、更加刺激的摩擦。
她的脚趾灵活得超乎想象,时而用趾腹夹住敏感的龟头,用力捻动;时而将两只脚的脚趾交错分开,形成一种紧密的包围,紧紧箍住柱身,上下快速地撸动;时而又用大脚趾的指甲,若有若无地刮搔着最脆弱的马眼和系带。
“呃啊……”方君忍不住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刺激太过激烈,几乎带着一种凌虐般的快感。他的身体在柔软的床垫上无助地扭动,想要逃离,腰肢却又不听使唤地向上挺送,追逐着那致命的接触。
与此同时,罂夫人的手也没有闲着。她一只手继续辅助着双足的动作,另一只手则抚上了自己高耸的胸脯,用力地揉捏起来,指尖掐着那挺立的乳尖,发出细微的、令人面红耳赤的喘息。在方君的视角里,她赤裸的身体因动作而微微汗湿,泛着情动的光泽,那双在他下身激烈动作的玉足,以及她自我抚慰的淫靡姿态,共同构成了一幅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将他的理智彻底摧毁。
快感再次如同潮水般积聚、比上一次更加凶猛、更加无法抗拒。在罂夫人双足更加激烈的刺激下,方君的身体绷紧如弓,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终于在一声短促的尖叫后,再一次猛烈地喷射出来。浓稠的精液大部分射在了罂夫人依旧在动作的双脚上,粘稠的白色液体玷污了那白皙的肌肤,顺着足弓和脚趾滴落。
释放之后,是极致的虚脱。方君的眼神彻底涣散,意识开始模糊。
罂夫人看着他那再次瘫软、几乎失去意识的样子,脸上闪过一丝尽在掌握的索然。她拿起那粉色药剂瓶,对着方君那饱经摧残、依旧微微颤抖的肉棒,随意地喷了一下。
“呃!”更加炽烈的灼烧感传来,方君发出一声短促的痛哼,眼前一黑,终于彻底陷入了昏迷之中。
罂夫人漠然地看着昏迷的方君,伸手拉动了床头一根精致的丝绒绳铃。
片刻后,一名穿着素净女仆装、表情恭顺却眼神空洞的女仆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给他清理一下,送回房间。”罂夫人懒懒地吩咐道,语气平淡得像是在处理一件无关紧要的杂物。
“是,夫人。”女仆低声应道,熟练地用床单裏住方君赤裸的身体,轻松地将他抱起,离开了这间弥漫着情欲和堕落气息的深红寝室。
门被轻轻关上。
昏暗的寝室内,只剩下罂夫人一人。她慵懒地躺回凌乱的大床上,眼神迷离地望着虚空。片刻后,她像是无法忍受那深入骨髓的空虚和饥渴,再次伸手,拿过了那根湿漉漉的假阳具。
同时,她另一只手抓过了那个之前被丢弃的、里面还残留着方君精液的飞机杯。她将杯口倾斜,对准自己红艳的嘴唇,微微晃动。
粘稠的、带着年轻男性气息的乳白色液体,缓缓流出,滴落在她的舌尖,然后被她一点点吞咽下去。她的喉头滚动着,脸上浮现出一种异常满足而又带着病态渴求的神情。然后,她将那假阳具再次对准自己依旧饥渴的身体,狠狠地刺入。
“嗯啊…·空旷昏暗的房间里,再次回荡起她放纵的呻吟,伴随着身体与橡胶摩擦的黏腻声响,久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