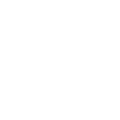沈三的腻烦,来得毫无征兆,却又合情合理。
当一个玩具的所有功能都被发掘,所有隐藏的彩蛋都被触发,当每一次的蹂躏都只能带来边际递减的快感时,丢弃,便是它唯一的宿命。
最后一个夜晚,是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地狱盛宴的终曲。
沈三似乎想要一次性榨干陆婉婷身体里最后一点可供娱乐的价值。
他命令凌宇,用那根最粗大的假阳具,塞满陆婉婷早已麻木的阴道。
然后,他自己则占据了那条被他亲手开辟出来的、如今已然松垮不堪的后庭之路。
而陆婉婷的嘴,则被另一根稍小一些的道具堵住,一直捅到喉咙的深处。
三穴贯通。
她像一个被插满了管线的实验仪器,躺在床上,无法动弹,无法发声,甚至无法顺畅地呼吸。
她所能做的,只是承受。
承受着阴道被冰冷硅胶撑开的撕裂感,承受着后庭被沈三的巨物碾磨的痛楚,承受着口腔和喉咙被异物填满的窒息。
沈三在这具被彻底工具化的身体上,发泄了最后一次。
他甚至没有让她高潮,因为那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征服,是展示,是宣告他对这具肉体拥有着绝对的、可以为所欲为的支配权。
当他像往常一样,粗暴地抽出自己的性器,并引发了她习惯性的直肠脱垂时,他脸上甚至没有了上一次那种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
他只是百无聊赖地戳了戳那朵翻出的「肉花」,就像一个顽童戳弄着一只死去的甲虫,然后便索然无味地结束了这一切。
凌宇像一个熟练的、毫无感情的护工,上前为妻子进行「复位」,清洗,上药。
陆婉婷则像一具尸体,全程没有任何反应。
第二天清晨,太阳照常升起。
当凌宇走出房间时,他发现客厅里空无一人。
沈三的房门大开着,里面的床铺整理得一丝不苟,仿佛从未有人住过。
那个属于沈三的、简单的行李包,消失了。
桌上,没有留下任何字条。
他走了。
这个认知,像一滴冰水滴入滚油,在凌宇和陆婉婷死寂的心湖里,炸开了一片混乱的蒸汽。
第一天,是恐惧。
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凌宇依旧在清晨将陆婉婷带去浴室「清洁」,虽然不再使用那些刺激性的液体,但流程一丝不苟。
陆婉婷则穿着沈三最喜欢的那件半透明的薄纱睡裙,像个幽灵一样在房间里飘荡。
她不敢画画,不敢看电视,甚至不敢坐得太久,生怕沈三在某个时刻突然推门而入,会因为她的「懈怠」而发怒。
第三天,是焦躁的期待。
每一次门外的脚步声,每一次楼道的电梯提示音,都会让他们的心脏猛地一抽。
凌宇会下意识地站直身体,陆婉婷则会本能地摆出那个屈辱的跪趴姿势。
然而,门铃始终没有响起。
希望一次次地燃起,又一次次地被死寂的空气浇灭。
一个星期过去了。
公寓里的气氛变得愈发诡异。
他们之间的交流几乎为零,但一种病态的默契却在两人之间流淌。
凌宇开始每天检查陆婉婷的后庭,为她涂抹修复药膏。
这不是出于爱护,而是一种维护「设备」的惯性。
他要确保,当「主人」回来时,这个「玩具」依旧处于最佳的使用状态。
而陆婉婷,则开始出现戒断反应。
她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高强度的刺激和痛楚。
如今,这突如其来的平静,反而让她无所适从。
她会在深夜里,因为身体莫名的空虚而惊醒。
她会无意识地用手指,去触碰自己那个已经松弛不堪、布满伤痕的穴口,仿佛在确认那段被侵犯的记忆是否真实存在。
没有了沈三的命令,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她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二个星期,等待已经变成了一种绝望的仪式。
他们不再期待门铃响起,但依旧维持着沈三在时的一切习惯。
这套被烙印进骨髓的奴役程序,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支柱。
他们就像两个被主人遗弃的宠物,依旧守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茫然地等待着那个永远不会回来的脚步声。
直到第十五天的早晨。
凌宇看着日历上那个被他悄悄画上的记号,终于,有什么东西在他那早已麻木的内心世界里,彻底崩塌了。
他缓缓地抬起头,看向坐在餐桌对面,同样面无血色、眼神空洞的陆婉婷。
他用一种干涩得仿佛几个世纪没有说过话的嗓音,说道:「他……不会回来了。」陆婉婷空洞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微弱的波动。
她慢慢地抬起眼,看着自己的丈夫。
「我们……」凌宇的嘴唇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自由?解脱?这些词语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和苍白。
他们没有获得自由,他们只是被丢弃了。
就像一个被玩坏、玩腻的玩具,被它的主人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甚至没有得到一句「再见」,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
他们的存在,对于沈三而言,无足轻重到连一个正式的告别都不配拥有。
这个认知,比任何酷刑和凌辱都更加沉重,更加具有毁灭性。
它彻底剥夺了他们在这场地狱游戏中,作为「对手」或「猎物」的最后一点价值。
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段无聊时光里的消遣品。
陆婉婷的眼中,缓缓地蓄满了泪水。
但她不是为自己的遭遇而哭,也不是为重获「自由」而哭。
她哭,是因为那份被抛弃的、一文不值的、深入骨髓的屈辱。
原来,被持续地、残忍地玩弄,还不是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是,连被玩弄的资格,都被收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