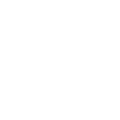第四十七章
我无力地坐到浴室门前。水声哗哗地响,像下着一场只有我们知道的雨。我呆呆地看着客厅,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想不了。窗外的光线一寸一寸暗下去。客厅里的影子从斜长变成模糊。门终于开了,冷气跟着涌了出来。她的脚步在门口停了一下,只有半秒。半秒里,我不知道她看了什么,也不知道她想了什么。然后她平稳地走向卧室,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跟上去,倚在门边。她背对着我,把叠好的衣服拆开,再叠一遍,很仔细。
“为什么?”她不说话。“苏霜,告诉我为什么。” 沉默像一堵墙,从她后背立起来,把我隔在外面。
我现在只想听她亲口说。说她厌烦我了,说我是累赘,说她后悔了。说什么都行。只要是她说的,我就认。我只要听到她亲口说就好.......可她什么都不肯说。
她站起身,拉着行李箱往门口走。我堵着门,她不说话,我不让开。我们就这么站着,像两棵挨得太近又彼此错开的树。晚饭我也没吃,她把菜热了一遍,端到桌子上,我不动。她又端走热,再端回来,反复几次。最后,她站在厨房门口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走过来,久到我准备好迎接任何一句话。可她只是转身,把菜放进冰箱。
她妥协了:“好,我陪你回老家。”
她不是不走。是换一种方式。
我不敢睡。坐在房间里,东看看,西看看。窗帘没拉,墙上的布袋被城市的灯照着。袋子印着的照片是那张。那个下午,她给我的警告。我盯着看了很久,然后移开目光。眯着眼睛,像睡,又不像睡。
第二天大早,我在客厅收拾带回来的东西。翻开柜子,看见一本病历,她的。我拿出来,刚翻开,余光里她正往外走,赶紧把病历塞进书包里。我要是不马上跟上,她是不会等我的。
高铁上,窗外的田野一片片往后跑,快得像在逃离什么。我把那个丝绒盒子拿出来,搁在小桌板上。她没回头。窗映着她的脸,眼睛垂着,一动不动。我看了很久。她始终没有转过来,似乎也在逃离什么。
那晚,我硬着头皮问了清卿姐,说为什么姐姐好像突然变了个人?她回答也不知道,“只是偶尔在花店里老说些有的没的。总是说生孩子什么的,反正有一段时间她总爱说这些.....我还笑她,三十出头的人,怎么说话像老太太。”
孩子.....孩子,我好像懂了,但我还是不敢确定。很想和她安安静静的聊、谈,可她不肯。每次我刚开口,她就站起身,说婶婶找她,说要去浇花,说该做饭了。她的背影总是走得很急,好像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
我只好去后山。到了后山才想起来那本病历,翻开,一页一页看过去,都是以前的。看得眼睛发酸,正准备合上,一张小单子从夹层里滑出来。几个月前的诊断......受育几率几乎为零。最开始那股尖锐的、割裂般的悲伤,化开了。
我想拿着这个诊断书拍她脸上,撕开她的伪装,但我依旧不敢肯定:她就是因为身体原因才离开的我。我怕我又鲁莽,以为稳操胜券......最后......
山风吹过来,把我吹的凉嗖嗖的。我坐着没动,等到太阳快落山才回去。
她眼底有青灰色的倦意,这几天她突然涂了粉,也盖不住。她每天早上还是给我炒饭,煎蛋。她那些小习惯也没有变,经常做一半才反应过来,我们的关系不是之前。倒冰快乐水时总是倒两杯,转身才反应过来,默默把另一杯一起喝了。切菜会下意识回头——从前我总是站在厨房门口等吃。然后她收回目光,继续切。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甚至想看看她的手机。机会来了。她去婶婶家拿东西,手机落在桌子上。屏幕亮着,一条消息弹出来又消失。我拿起来。密码依旧是我的生日。那些软件,那些聊天记录,都在那儿,只要我点开。我看着她的桌面,很久。她信我。我却——我把手机放回原处。其实,密码还是我的生日就已经足够了。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猜想,我开始有意无意的说这个新房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她会竖着耳朵听,也会跟着我到处看看。我故意说这里不好看,她会看一下手机然后马上说:“这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随即又不说话了,嘴唇抿起来,像说错话的小孩。有时候我说这里的布置很美,她脸上会浮起温柔的笑,似乎在说:“我弄得还不错吧?”,像在等待奖励的小孩。
我就知道,她就是装不爱我的,她从想着离开。只是因为“不想拖累你”,这也正是她这些天不敢和说的。或许从她答应我回来那一刻起,我就应该意识到的。只是那时什么也不愿去想。
她现在这样子有独特的美。想隐藏却又暴露着,像雾天里的山,隐隐约约,可我现在就在山上。这样对她来说,太痛苦了。我必须结束它。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让她告诉我答案。
那个下午,我用“我的未来”作为饵,她毫无意外的上了钩。
后山,我等了很久。等到风停下来,蝉也不叫了。等到夕阳沉下去一半,把她的脸映得暖红。等到她站起来要走。然后我吻了她。不是请求,也不是试探。是压了太久的、近乎凶狠的吻。
“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苏霜。”
“你还装吗?”
她终于装不下去了,在我怀里大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浴室里的水声。她整个人软下去,如果不是我抱着,大概会滑到地上。她依旧这么瘦弱,怕是想那些无关我们之前的事情太多吧。
如果她还能继续装下去,还继续强撑……
那我可能会说最毒辣的话语:“你说你是妈妈?好!那你就该眼睁睁看着我这个儿子去死吗?!你敢再推开我一次……你敢再逃……我现在就去买药!再吃一遍!我说到做到!苏霜!我只要你活着!在我身边!生不了孩子我也要!是累赘我也背!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
当前提是:她是装的。
很久,在夜风下,她才慢慢平静下来。之前我也不是没想过未来,但一想到孩子,就停住了——用“现在还太早”打断自己。可有的事,我现在必须全说出来,让她安心。
“你记得村里那家吗?他爸妈……”我没有说下去。她也知道。他爸妈是兄妹,当年一直跪着求爸妈,又因为那时依旧怀了才同意。他们的好几个孩子都夭折了,现在的那个……三十多了,每天坐在村口晒太阳,看见人就嘿嘿地笑。智商只有六岁孩子。
我们的孩子如果也那样,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想,她如何接受自己的孩子离开世界……
“我们的孩子……就算健康。他要用多少年来消化我们的故事?他会不会恨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从出生就背负着一道原罪?孩子是爱的结晶——我不信。我要的只有我们。我不是吃醋,只是不想让我们的爱,还要别的东西来证明。”
我们的爱,诞生于泥泞与禁忌,本身就带着无法言说的不幸。将一个无辜的生命,硬生生拽入这晦暗不明的漩涡……这公平吗?
“如果你真的想要,以后我们可以想办法。别担心了好吗?”
她沉默了很久。夜风从山坳那边吹过来,带着夏夜的凉意。她把脸埋进我的颈窝,声音闷闷的,带着哭过后的沙哑。“我们不要了……小川。”
我听出她语气里的不甘。她分明还是想要的,其实还是因为她自己还接受不了自己身体的原因。大概就是:“你可以不要,当我不能没有”的意思。我抱着她,在夜风里坐了很久。久到月亮升上来,把整片草地照成银白色,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第一野战……”我忽然开口,“感觉怎么样?”她愣了一下,然后猛地从我怀里弹起来,脸很烫,大概红透了。“走了走了,被蚊子咬了!”她走得飞快,像逃,背影渐渐没入夜色。我坐在原地,看着那个方向,淡淡笑了。
白天,我成了她最笨拙的影子。“姐姐,这个重,我来。”“那块地不平,走这边。”“小心烫,慢点拿。”这些话自己从嘴里跑出来,收不住。我知道她是太累了。身体会坏,是因为她一个人扛了太久太久。她总是什么都不说,把所有重量都压在自己肩上。在她眼里,我不是丈夫,是孩子。她不想给孩子包袱。
“小川,没事。你休息。”
她总回我一个清浅的、带着安抚的笑。
可到了夜晚,那个克制的、小心翼翼的苏霜就不见了。她像倦鸟归林,把自己完整地投进我怀里。她的吻不再是白日里蜻蜓点水的安抚,而是带着近乎贪婪的掠夺。像是要把白天所有的克制,都在这时候补回来。
“小川……”她这样唤我,声音低哑,像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叹息。这两个字被她喊得百转千回,瞬间把我的心揉皱。
“姐姐……我在……”
当情欲的潮汐退去,她蜷缩在我怀里,脸颊贴着我的胸膛,呼吸渐趋平稳。我低头看着她,她偶尔抿抿嘴,不知道在梦里看见了什么。
为了让她多高兴点,我偷偷联系了清卿姐,她来的时候,是午后。她的笑声从村口下车一路撞进来,“小川!小霜!给你们带了好吃的!”
新房什么都好,就是房间少。两个正经卧室,一个书房,再没有多余的床。趁清卿姐在院子里看凤仙花,她一把将我拽进里屋。
“小川!”她压低声音,又急又快,脸颊绯红,带着做贼似的慌乱。“我感觉……清卿姐肯定……”顿了顿,“而且……就两个卧室。清卿姐来了,我……我得去跟她挤客房。所以……这几天晚上,你给我老实点!听见没?”她戳我胸口,一下,两下。
“晚上不许弄出动静!更不许偷溜!不然姐姐真的会哭的!”
这副又羞又急、偏还要强撑“姐姐”威风的模样,可爱得让我差点笑出声。“知道了。”我一本正经地点头,“我会很老实的。” 她狐疑地看我一眼,红着脸快步出去了。
白天,她被我一个隐晦的眼神撩得瞬间脸红,还要强装镇定与清卿姐谈笑。清卿姐暂时出去的时候,她会狠狠瞪我一眼,用口型说:“老实点!” 我无辜地摊手,她气得起身就跟着出去,耳朵红红的。那强忍的羞意和眼底的水光,比任何夜晚的放纵都更让我心痒难耐。
然而真正让我心落定的,是另一幕。那天在田间溪畔,她带清卿姐认野菜。她挽着袖子,利落地翻开石头。“清卿姐你看,这种菜最嫩——” 她神采飞扬,眉眼里全是光。
那一刻,她不是那个躲在浴室里无声哭泣的女人,不是那个把忧虑都压在眼底、笑着给我做饭的姐姐。是那个牵着我的手走山路的小姑娘。是那个在黎明里离开、背影却从不佝偻的人。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她。无比清晰地认识到:她拥有一颗远比我想象的更辽阔强大的心。她不需要我做她的盾牌,也不需要我做她的拐杖。她要的,是并肩看这个世界的伴侣,是爱与信任。
而她,必将带着这份浴火重生的力量,将她的人生踏踏实实、光芒万丈地走下去。
这份笃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心,以及为她升腾起的无与伦比的骄傲——为她的不屈,为她的光芒,为她是我独一无二的苏霜。
清卿姐在远处招手:“小川!发什么呆!过来帮忙摘!”
她跟着回头看我一眼,眼里有光,唇角有笑。那一眼里,有千言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