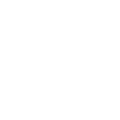1.性感女郎的约会邀请
周一的早晨反常地安静。
我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看着旁边空着的座位。横山丽辉的椅子整齐地推在桌下,桌面上干干净净,没有摊开的课本,没有随手放的笔袋。第一节课的铃声已经响过五分钟,老师开始讲解三角函数,但那个座位依然空着。
这不是丽辉的风格。他是那种会提前十分钟到校,预习当天课程的好学生。即使生病,他也会在前一晚发消息告诉我。
课间休息时,我拿出手机查看。没有消息。我犹豫了一下,给他发了条简短的信息:“今天不来?”发送后,消息状态很快显示“已读”,但没有回复。
一种微妙的违和感在胃里蔓延。我想起周六早晨他离开时眼中的光芒,想起他问“她约会吗”时的语气,想起母亲听到他家庭背景后那若有所思的微笑。
第二节课开始前,我借口去卫生间,走到走廊尽头拨通了母亲的号码。铃声一遍遍响着,机械的女声最终告诉我:“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我挂断,盯着手机屏幕。上午十点十七分。母亲通常在这个时间刚起床不久,如果昨晚酒吧没有特别活动,她应该在家。但周六晚上她说要去酒吧参加常客的生日会,也许她回来得很晚,也许......我回到教室,却无法集中注意力。黑板上的数学公式变成模糊的符号,老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丽辉的空座位像一个无声的质问,母亲未接的电话则是另一个。
第三节课上到一半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举手,低声告诉老师我胃痛得厉害,需要去医务室。老师关切地看着我苍白的脸——这倒不是伪装,紧张让我的脸色确实不好——点了点头。
我没有去医务室。我直接走向校门,门卫问我时,我出示了医务室的假条——那是上周我感冒时开的,一直放在书包里。门卫扫了一眼,挥手让我通过。
走出校门,四月的阳光明亮得刺眼。街道上车辆稀疏,几个主妇推着婴儿车走过。我站在路边,突然不确定自己该去哪里。回家?如果母亲不在,空荡的公寓只会加剧我的不安。去酒吧?也许她在那里。
我选择了后者。
公交车空荡荡的,只有几位老人和带着购物袋的主妇。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商店街的招牌,自行车上的学生,便利店前抽烟的工人。平凡的世界继续运转,而我正驶向某个可能打破这种平凡的发现。
“月昙”在白天看起来毫无魅力。深色的木门紧闭,紫色霓虹灯招牌熄灭着,窗户依然被厚重的窗帘遮挡。它像一只沉睡的兽,夜晚才会苏醒并露出獠牙。
我推了推门,锁着。绕到侧面小巷,后门也紧闭。正当我犹豫时,旁边美容院的门开了,一个年轻女人走出来抽烟。我认出她是酒吧的前台接待,薰小姐。
“雅人?”她惊讶地看着我,“这个时候你怎么在这里?不用上学吗?”“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我说,走近她,“薰姐,看到我妈妈了吗?她电话打不通。”薰小姐吸了口烟,眼神有些闪烁。“雅子姐啊......她上午来过,但很快又走了。”“去哪里了?”“和一个年轻男生一起出去的。”薰小姐弹了弹烟灰,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暧昧,“说是去附近的樱花林走走。那男生看着挺年轻的,高中生吧?但长得不错,个子高,穿白衬衫......”她描述的形象清晰地指向一个人。我的胃部收紧。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大概九点半?”薰小姐看了看手表,“对,我刚来上班不久他们就走了。雅子姐今天穿得特别年轻,我都差点没认出来。水手服哦,超短裙,头发还扎成双马尾。真敢穿......”水手服。超短裙。双马尾。
这些词在我脑海中组合成一个荒谬的图像。母亲,四十三岁的母亲,酒吧老板母亲,穿着高中生的制服,和我的同学去了樱花林。
“谢谢。”我说,声音干涩。
“你没事吧?脸色真的很差。”薰小姐关切地问。
我摇摇头,转身离开。走到街角时,我听见她在身后喊:“要不要进来坐坐?我给你倒杯水......”我没有回头。
樱花林在城市的东边,乘坐公交车需要二十分钟。我坐在摇晃的车厢里,看着手机屏幕上依然没有回复的消息,看着母亲依然无法接通的号码。窗外的景色从商业区逐渐变为住宅区,然后是开阔的河岸和公园绿地。
四月中旬,樱花已过了最盛的时期,开始飘落。公交车驶过河道时,我能看见两岸粉色的云霞和随风飞舞的花瓣。樱花林公园是本地有名的约会地点,每年这个时候都挤满了情侣和赏花家庭。但现在是周一上午,人应该不多。
我在公园入口下车。果然,停车场只停着几辆车,入口处的告示牌显示着樱花祭的活动已经结束。我买票进入,踏上铺满花瓣的小径。
公园里安静得只有鸟鸣和风声。偶尔有老年人散步,推婴儿车的母亲,遛狗的人。樱花树连绵成片,地上铺着一层粉白色的花瓣,像柔软的地毯。阳光透过花枝洒下斑驳的光影,美得不真实。
我沿着主径道走着,眼睛扫视着四周。薰小姐说他们来樱花林,但这么大的公园,怎么找?我放慢脚步,思考着如果是母亲,她会选择什么地方。
她会选择风景优美但相对私密的地方。有水的地方,有长椅的地方,能展示她的“新造型”又能营造浪漫氛围的地方。
我转向通往神社的小径。那里有古老的鸟居,石灯笼,许愿牌墙,还有几棵特别巨大的樱花树。母亲喜欢有故事的地方,喜欢能拍照发社交媒体的背景。
小径逐渐上升,石阶上落满花瓣。我走得很轻,像害怕惊扰什么。转过一个弯,神社的红色鸟居出现在眼前。然后我看见了他们。
在鸟居旁的巨大樱花树下,母亲和丽辉并排站着,仰头看着如雪般飘落的花瓣。
我停住脚步,躲在一棵树后。
母亲今天确实穿着水手服。不是那种廉价的情趣服装,而是质地上乘、剪裁合体的深蓝色制服,配白色衬衫和红色领巾。裙子短得惊人,离膝盖有很长的距离——不,那不是普通的高中制服裙,是特意改短过的版本。她的腿上没有穿丝袜,白皙的皮肤完全裸露,在阳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泽。
最令人震惊的是她的发型。栗色长发扎成了双马尾,用红色的丝带系着,垂在肩头。她甚至戴了一副平光眼镜,增添了“清纯学生”的伪装。
但她的身体无法伪装。水手服的上衣在她胸前绷紧,勾勒出饱满的曲线;短裙下的臀部浑圆挺翘;裸露的大腿修长笔直,肌肉线条优美。这是一个成熟女性的身体,强行塞进少女的服装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既可笑,又诡异,又带着某种危险的诱惑。
丽辉站在她身边,穿着整洁的白色衬衫和卡其裤,头发梳理整齐。他手里拿着一个相机,正对着母亲拍照。母亲摆出各种姿势:双手捧脸微笑,侧身回眸,转圈让裙摆飞扬。每个动作都刻意模仿少女的天真,但由她做出来,却有一种精心计算的表演感。
“这张好可爱!”丽辉看着相机屏幕说,声音里有我从未听过的兴奋。
“真的吗?”母亲小步跑过去,凑近看屏幕。她的身体几乎贴着他的手臂,双马尾的发梢扫过他的肩膀。“哎呀,这张脸拍得有点大......”“不会,很漂亮。”丽辉认真地说,然后转向她,“雅子阿姨,你穿成这样真的像高中生。”“叫姐姐。”母亲用手指轻轻戳他的额头,“今天我不是阿姨,是姐姐哦。”丽辉笑了,耳朵发红。“雅子......姐姐。”“乖。”母亲满意地笑了,然后转了个圈,“这套衣服是特别定制的,花了不少钱呢。但为了今天,值得。”“为什么是今天?”丽辉问。
母亲停下动作,看着他。樱花从他们头顶飘落,有几瓣落在她头发和肩头。这一刻,在花瓣雨中,穿着水手服的她看起来居然有一种虚幻的美,像从另一个时空误入此地的幻影。
“因为今天是你第一次逃课约会呀。”她说,声音轻柔,“值得纪念的日子,当然要特别一点。”“我其实有点紧张。”丽辉承认,“第一次逃课。”“我也是第一次穿成这样。”母亲说,走近一步,抬头看他。他们的身高差让这个动作显得格外亲密。“我们都做了平时不会做的事,不是很浪漫吗?”丽辉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她。他的目光从她的眼睛移到嘴唇,再到水手服领口露出的锁骨,再到短裙下的大腿。那目光里有迷恋,有困惑,有十七岁少年面对成熟女性诱惑时的无措。
母亲伸手,轻轻摘掉他肩头的一片花瓣。动作缓慢,手指有意无意地擦过他的颈侧。
“丽辉君喜欢樱花吗?”她问。
“喜欢。”“樱花很短暂呢。”母亲看向满树繁花,“盛开时绚烂无比,但一阵风吹过,就纷纷飘落。人生中美好的事物大多如此——短暂,易逝,所以要紧紧抓住。”她转回视线,看着他。“你明白吗?”丽辉点头,眼神专注。“我明白。”“那你会抓住美好吗?”母亲问,声音更低,更柔。
“......我会试试。”母亲笑了,那笑容里有胜利的预兆。她拉起他的手。“来,我们去写许愿牌。听说这里的姻缘很灵验。”他们走向神社前的许愿牌墙,手牵着手。母亲走在他身边,双马尾随着步伐晃动,短裙下的腿在阳光下白得耀眼。她走路时微微扭动臀部,那是她多年习惯的步态,即使穿着水手服也无法完全掩饰。
我躲在树后,看着他们挑选许愿牌,看着丽辉付钱,看着他们背对着我写字。母亲写得很认真,侧脸专注;丽辉不时偷看她,脸上有抑制不住的微笑。
他们写完后,将木牌挂在墙上众多许愿牌之中。然后母亲拿出手机,拍下两人的许愿牌,又拉着丽辉自拍。她靠在丽辉肩上,比出剪刀手,笑容灿烂得不真实。丽辉看起来有些僵硬,但眼神明亮。
“许了什么愿?”母亲问。
“说出来就不灵了。”丽辉说。
“也是呢。”母亲点头,然后凑近他耳边,低声说了什么。我看见丽辉的耳朵瞬间红透,眼神闪烁。
他们在神社前的长椅上坐下。母亲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便当盒——粉色的,系着丝带,像女高中生精心准备的约会便当。
“我早上做的。”她说,打开盒子。里面是精致的饭团、玉子烧、炸鸡块、小番茄,摆成可爱的图案。“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看起来很专业。”丽辉说。
“以前学过的。”母亲递给他一双筷子,“为喜欢的人做饭,是件幸福的事。”她说“喜欢的人”时,眼睛直视着他。丽辉接过筷子的手微微颤抖。
他们开始吃东西。母亲小口小口地吃,不时用手帕擦嘴,动作刻意地优雅。丽辉吃得比较快,但每当母亲说话时,他就会停下来认真听。
“雅人小时候也喜欢来这个公园。”母亲突然说,声音里有一丝怀念,“他父亲还活着时,我们经常一家三口来赏樱。那时候樱花好像比现在更美。”这是谎言。父亲从未带我们来过这里。他在我五岁时就逃跑了,而我对他的记忆模糊不清。但母亲说得如此自然,如此深情,连我都差点相信了。
“雅人很辛苦吧。”丽辉说,语气真诚,“你一个人把他带大。”“辛苦,但值得。”母亲微笑,笑容里恰到好处地掺杂着一丝坚强与脆弱,“有时候我也会累,也会想依靠谁。但生活不允许。”她低下头,看着手中的饭团。这个姿态让她显得脆弱,需要保护。丽辉的手抬起来,似乎想碰触她的肩膀,又在半空中停住。
“如果......如果你需要,”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可以......”“你可以什么?”母亲抬头看他,眼睛湿润。
“可以帮助你。”丽辉终于说完整,“以任何方式。”母亲看着他,然后笑了,那笑容像阳光穿透云层。“你真是个温柔的孩子。但你还小,不应该承担这些。”“我不小了。”丽辉反驳,声音里有少年的倔强,“我已经可以自己决定很多事情。”“比如逃课约会?”母亲调侃。
“比如选择想见的人。”丽辉认真地说。
他们之间的空气变得粘稠。樱花继续飘落,落在他们头发上、肩膀上、便当盒旁。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但这里像一个被隔离的泡泡,只有他们两个人。
母亲伸出手,轻轻拂去丽辉头发上的花瓣。她的手指停留在他发间,然后慢慢滑到他的脸颊。
“你的皮肤真好。”她轻声说,“年轻真好啊。”“雅子姐姐也很年轻。”丽辉说,声音有些沙哑。
“真的吗?”“真的。”他们的脸靠近了。我屏住呼吸,手指不自觉地抓住树干。树皮粗糙的触感让我保持清醒,提醒我这不是梦。
但就在嘴唇即将接触的瞬间,母亲退开了。她站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花瓣。
“差不多该回去了。”她说,声音恢复了平常的轻快,“你还要回学校吧?”丽辉看起来有些失望,但也站起来。“嗯,下午还有课。”“那我送你到车站。”母亲说,开始收拾便当盒。
我迅速后退,躲到更隐蔽的地方。看着他们并肩走下石阶,母亲自然地挽住丽辉的手臂,头靠在他肩上。这个姿势让她看起来更娇小,更依赖他。丽辉挺直了背,像个保护公主的骑士。
他们消失在樱花小径的尽头。我站在原地,看着空荡的神社前庭,看着那满墙的许愿牌在风中轻轻摇晃。
我慢慢走过去,寻找他们的木牌。很快找到了——挂在一起的两个,用红绳系着。
丽辉的写着:“愿重要的人永远幸福。”字迹工整,像他的为人。
母亲的写着:“愿樱花般的缘分永不凋零。”字迹优雅流畅,旁边还画了一朵小小的樱花。
我盯着那块木牌,突然想起薰小姐的话:“真敢穿......”是的,她真敢。敢穿水手服扮少女,敢勾引儿子的同学,敢在许愿牌上写下“缘分”这样的词。她敢把一场精心策划的狩猎包装成浪漫邂逅,敢用谎言编织陷阱,敢在阳光下进行黑暗的交易。
但丽辉看不出来。他看见的是美丽的樱花,是穿着制服显得年轻可爱的“姐姐”,是便当和温柔的话语。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女人,一个理解他的成熟女性,一个与学校里那些幼稚女生完全不同的人。
他不知道这套水手服的价格可能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零花钱,不知道这些台词演练过多少次,不知道便当可能是便利店买来重新装盒的。他不知道这场“浪漫约会”是一场表演,而他是唯一的观众兼猎物。
我转身离开神社,沿着另一条小径下山。樱花还在飘落,轻柔地,无情地。地面上的花瓣越来越厚,踩上去没有声音。
回到公园入口时,我看了看时间: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回学校还能赶上下午的课。但我没有走向公交车站,而是走向河岸。
我在河边长椅上坐下,看着流淌的河水。水面漂浮着樱花花瓣,像粉色的眼泪。远处,城市的轮廓在春日阳光下清晰可见。
手机震动。我拿出来看,是母亲的消息:“中午不回家吃饭,酒吧有事。冰箱里有剩菜可以热着吃。”简洁,平常,像任何一位母亲发给儿子的消息。
我没有回复。我又打开与丽辉的聊天界面,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我发的“今天不来?”,状态是“已读”。
我盯着那个界面,手指悬在键盘上。我想警告他,想告诉他真相,想把他从这个危险的游戏中拉出来。
但我最终什么也没打。我关掉手机,放回口袋。
河风吹过,带着樱花和河水的气息。我靠在长椅上,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是母亲穿着水手服转圈的样子,是她靠在丽辉肩上的样子,是她写下“愿樱花般的缘分永不凋零”的样子。
以及丽辉看着她的眼神——那种被蛊惑的、沉迷的、心甘情愿踏入陷阱的眼神。
樱花的花期只有两周。两周后,这些绚烂的花朵将全部凋谢,树枝重新变得光秃。但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不会随着樱花凋谢而结束。
它会生根,发芽,生长,最终结出无人能预料的果实。
我站起身,拍掉身上的花瓣。该回学校了,该回到那个丽辉缺席的教室,该继续扮演普通的高中生,该假装我不知道今天上午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我看见了。而我选择了沉默。
沿着河岸走向公交车站时,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樱花林。那片粉色的云霞在正午阳光下灿烂得刺眼,像一场盛大而短暂的梦。
梦会醒。但醒来时,现实可能比梦更荒谬。
公交车来了。我上车,投币,坐下。车辆启动,樱花林渐渐后退,缩小,最终消失在建筑物之后。
我靠着车窗,看着自己的倒影。一个逃课的高中生,一个沉默的共犯,一个目睹母亲狩猎自己朋友却无力阻止的儿子。
倒影中的少年眼神疲惫,嘴角紧抿。
他知道游戏已经开始,而所有人,都已经踏入棋盘。
深夜一点十七分。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的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综艺节目里的艺人们夸张地大笑,罐头笑声一波波涌来,填补着公寓里过分的安静。茶几上摊着几本摊开的习题集,笔躺在纸页间,墨迹早就干了。我维持这个姿势已经三个小时,像一尊等待的雕像。
母亲没有回来。没有电话,没有消息。
下午从樱花林回来后,我勉强赶上了最后一节课。教室里的空气闷热,数学老师在讲解向量,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抽象的箭头。我盯着旁边的空座位,丽辉整个下午都没有出现。放学时,几个女生围在一起低声议论:“横山君今天请假了吗?”“不知道,发消息也没回。”
我收拾书包的速度很慢,故意拖到最后才离开。校门口,穿着其他学校制服的女生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新开的甜品店,上班族们步履匆匆地走向车站。平凡的世界照常运转,而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偏离轨道。
回到家时,公寓空无一人。母亲通常会在下午四点左右起床,为晚上的酒吧工作做准备。但今天她的卧室门紧闭,里面没有声音。我敲门,没有回应。拧动门把,锁着。
厨房冰箱上贴着一张便签,是她潦草的字迹:“晚上有特别活动,晚归。自己吃饭。”没有具体时间,没有说和谁一起,没有说是什么活动。
我热了昨天的剩菜,独自吃完,洗碗,写作业。八点,九点,十点。窗外的天空从深蓝变成墨黑,对面大楼的窗户一盏盏亮起又熄灭。我打开电视,让声音填充沉默。
十一点时,我做了件之前从不会做的事——我打开了丽辉的Instagram账号。我们互相关注,但很少互动,他的主页大多是风景照、读书笔记,偶尔有和家人的合影,标准的好学生记录。
但今晚,他的主页变了。
最新的一条动态发布于两小时前,是一张夜景,霓虹灯模糊成光斑,配文:“不一样的夜晚。”下面已经有几十个点赞和评论:“哇,这是哪里?”“横山君今天没来学校就是去这里了吗?”“看起来好高级!”
我往下滑动。
然后停住了呼吸。
最新的一系列照片全是她。母亲。或者说是“雅子姐姐”,正如丽辉在标签里写的那样:“#和漂亮的邻居姐姐一起 #特别的一天 #摄影练习”。
第一张:母亲坐在高级餐厅的靠窗位置,穿着黑色露肩连衣裙,裙摆短至大腿中部。她侧身对着镜头,一只手托腮,眼神迷离地望着窗外的夜景。灯光在她裸露的肩膀和锁骨上投下柔和的阴影,嘴唇上的口红在暗调照片中鲜艳如血。丽辉的备注:“姐姐说这家餐厅的夜景是全城最好的。”
第二张:母亲站在某个精品店的试衣镜前,穿着一套米白色套装——紧身短上衣和包臀裙。上衣的扣子只系到胸部下方,露出深深的乳沟和纤细的腰身;裙子紧贴臀部曲线,在膝上十公分处戛然而止。她对着镜子自拍,手机遮住了半张脸,但那双眼睛透过镜头直直看向观看者,带着挑衅的笑意。备注:“姐姐试衣服的样子让我心跳加速。”
第三张:母亲在某个灯光昏暗的场所,背景模糊但能看见吧台和酒架。她跨坐在一张高脚凳上,姿势大胆——一条腿伸直脚尖点地,另一条腿弯曲,膝盖几乎碰到胸口。她穿着银色亮片吊带和黑色热裤,吊带低胸设计,乳沟毕现;热裤短得几乎只能遮住臀部,大腿完全裸露。她的身体向后仰,一只手撑在凳子上,另一只手举着酒杯,长发散乱。备注:“姐姐说这是她年轻时最喜欢的姿势。”
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照片越来越多,尺度越来越大。有一张是母亲在某个看起来像夜店舞池的地方,周围是闪烁的灯光和模糊的人影。她背对镜头,回头望来,上半身只穿着黑色蕾丝内衣,下半身是破洞超短牛仔裤,裤腰低至髋骨,露出一截白皙的腰臀曲线。她的臀部浑圆挺翘,在紧身内衣和短裤的包裹下形成完美的桃形。备注:“姐姐跳舞的样子像专业dancer。”
另一张更露骨:母亲靠在某个豪华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是城市夜景。她面对镜头,只穿着白色衬衫——明显是男式衬衫,过大,只系了中间两颗扣子,衣襟敞开,露出里面的黑色蕾丝内衣和平坦的小腹。衬衫下摆刚好遮住臀部,双腿完全裸露,又长又直,在夜色中白得发光。她一只手撩着头发,眼神慵懒诱惑。备注:“借用我的衬衫,她说这样穿舒服。”
我一张张往下翻,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得越来越快,呼吸却越来越慢。照片里的母亲展现了我不曾见过的各种面貌:清纯的,性感的,高冷的,火辣的。在丽辉的镜头下,她时而像邻家姐姐般亲切,时而像夜店女王般狂野,时而又像高级交际花般神秘。但无论哪种形象,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性感的、可供消费的、精心包装的女性身体。
评论区的留言在不断增长:
“这是谁啊?好漂亮!”“横山君交女朋友了?年上系?”“身材也太好了吧!”“求介绍!”“这真的是‘邻居姐姐’?看起来不太像啊......”
丽辉只回复了其中几条,用暧昧不清的语气:“是特别的人。”“不能介绍哦,是专属模特。”“年龄是秘密~”
专属模特。这个词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退出Instagram,打开通讯录,找到丽辉的号码拨过去。铃声一遍遍响着,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人接时,电话通了。
“喂?”背景音嘈杂,音乐声、人声、玻璃碰撞声混在一起。
“丽辉,你在哪?”我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
“啊,雅人?”他的声音有些飘忽,像是喝了酒,“我在......在外面。”
“和谁一起?”
“和......朋友。”他含糊地说,“有事吗?”
“今天你没来学校。”
“嗯,请假了。”他简短地回答,“有点事。”
背景里传来女性的笑声,尖锐而熟悉。我握紧了手机。
“你是不是和我妈在一起?”我直接问。
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音乐声似乎小了些,可能他走到了安静的地方。“雅人,你听我说......”
“回答我。”
“......我们在逛街。”他终于说,声音低了下去,“雅子姐姐带我看看夜景,买点东西。她很好,你不用担心。”
逛街。在深夜一点?穿着内衣在夜店跳舞叫逛街?
“丽辉,你......”
“抱歉,我得挂了。”他急促地说,“晚点再联系你。”
电话断了。我盯着手机屏幕,那通两分钟不到的通话记录像一个小小的讽刺。我再次拨打,直接转入语音信箱。打给母亲,同样无人接听。
我扔开手机,双手捂住脸。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微光和窗外的城市灯火,寂静像实体一样压下来。我想起樱花树下母亲穿着水手服的样子,想起她写在许愿牌上的“缘分”,想起她说“抓住美好”时的表情。
那不是美好。那是陷阱。而丽辉已经一脚踏了进去,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
时间继续流逝。一点,一点半,两点。电视节目早已结束,深夜购物广告开始循环播放,主持人用亢奋的语气推销着美容仪和健康食品。我关掉电视,黑暗彻底笼罩房间。
就在我几乎要在沙发上睡着时,楼下的街道传来了出租车的声音。
引擎声由远及近,最后停在了我们公寓楼前。车门开关的声音,含糊的说话声,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踉跄的,不稳的。
我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楼下,母亲正从出租车里扶出一个人。街灯的光线昏暗,但我能认出那是丽辉。他几乎完全靠在母亲身上,脚步虚浮,头低垂着。母亲一手架着他的胳膊,另一只手关上车门,出租车驶离。
他们摇摇晃晃地走向公寓入口。母亲今天穿着照片里那件黑色露肩连衣裙,裙摆在夜风中飘动。即使从三楼看去,我也能看见她裸露的肩膀和大腿在灯光下白得晃眼。丽辉的白色衬衫皱巴巴的,领口敞开。
我放下窗帘,走到玄关等待。
钥匙转动的声音格外缓慢,试了好几次才打开。门推开时,母亲先探进半个身子,看见我站在黑暗中,她愣住了。
“雅人?你还没睡?”她的声音带着醉意,但努力保持清醒。
“在等你。”我说,没有开灯。
她完全推开门,费力地把丽辉拖进来。丽辉已经完全醉了,眼睛半闭,嘴里含糊地嘟囔着什么。他的手臂搭在母亲肩上,整个人的重量压向她。母亲的高跟鞋在玄关的地板上踉跄了一下,她低声咒骂了一句,用力把他往客厅拖。
“帮个忙。”她对我说,喘着气。
我没有动。“你们去哪了?”
“先帮忙把他弄到沙发上去。”母亲的声音里有了命令的语气。
我沉默了几秒,最终还是走过去,架起丽辉的另一只胳膊。他浑身酒气,混合着烟味和陌生的香水味——可能是夜店里的味道。我们合力把他拖到沙发边,他瘫倒下去,头歪向一边,几乎立刻发出了鼾声。
母亲直起身,揉着肩膀。她的头发散乱了,妆容有些花,口红晕到了嘴角外。黑色连衣裙的肩带滑下一边,露出半个胸罩的黑色蕾丝边。她注意到我的目光,随手把肩带拉回去,动作漫不经心。
“累死了。”她踢掉高跟鞋,赤脚走向厨房,“这小子酒量太差,才几杯就成这样。”
“你们去哪了?”我重复我的问题,声音在安静的公寓里格外清晰。
母亲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水,仰头喝了几口。水顺着她的下巴流下,滑过脖颈,消失在领口深处。她喝完,用手背擦了擦嘴。
“银座,六本木,几个高级俱乐部。”她说,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丽辉君今天可大方了,餐厅、购物、夜店,全是他买单。”
她走回客厅,从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购物袋,拿出里面的东西——一条蒂芙尼的项链,吊坠在黑暗中闪着微光。
“看,他送的。”她把项链举到灯光下,“还有这个。”又拿出一瓶香奈儿香水,“和这个。”一副普拉达的太阳镜。
她像展示战利品一样把这些东西摊在茶几上。奢侈品的光芒在昏暗的光线下冰冷而刺眼。
“花了多少钱?”我问。
母亲想了想,笑了。“餐厅大概八万,购物十五万,夜店开台加酒水......十二万?差不多三十五万日元吧。”
三十五万日元。一个高中生一个月的零花钱可能只有几万,三十五万对他来说绝不是小数目。但他花了,为了她。
“收获满满的一天。”母亲总结,满足地叹了口气。她坐倒在单人沙发上,双腿伸直,裙子完全滑到大腿根部。她没穿丝袜,腿完全裸露,在月光下泛着瓷白的光泽。
我盯着沙发上醉得不省人事的丽辉,又看向满脸得意的母亲。一股冰冷的愤怒从胃部升起。
“那代价呢?”我问,声音平静得可怕。
母亲正在检查项链的扣环,闻言抬起头。“什么?”
“代价。”我重复,“他花了三十五万,你给了他什么作为交换?”
母亲的表情僵住了。她放下项链,眼神锐利起来。“雅人,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我向前走了一步,“你给了他什么?他付了钱,你提供了什么服务?陪酒?陪笑?还是......”
我停顿,目光从她裸露的肩膀移到胸部,再到大腿。
“还是你给他上了?”
空气凝固了。
母亲慢慢地站起来,动作里有种危险的缓慢。她走近我,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即使喝醉了,她的气场依然强大,那是多年在男人堆里周旋练就的本能。
“注意你的措辞。”她低声说,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我是你母亲。”
“那你就像个母亲的样子。”我回击,声音终于控制不住地颤抖,“而不是穿着内衣让我同学拍照,不是在夜店跳舞,不是把他的钱榨干后拖着他的尸体回家!”
“我没有榨干他。”母亲冷静地说,“是他自愿的。他说想让我开心,想给我买礼物,想看我穿漂亮的衣服。我给了他机会。”
“你给了他幻想。”我纠正,“你让他以为你是什么‘邻居姐姐’,以为这是一场浪漫的约会,以为你们之间有‘特别的缘分’。但他不知道你同时在计算他花了多少钱,不知道你在评估他的价值,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表演!”
母亲的脸色彻底冷了。“表演又怎样?我让他开心了,不是吗?你看看他——”她指向沙发上熟睡的丽辉,“他今天笑得像个孩子。他给我拍照时眼睛在发光。他为我花钱时心甘情愿。我给了他一个美好的夜晚,他给了我物质回报。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对?”
“他是我的同学!”我几乎吼出来,“他才十七岁!你四十三岁了!这不对!这恶心!”
“恶心?”母亲笑了,那笑容冰冷而扭曲,“那什么是高尚的?像你亲生父亲一样逃跑是高尚的?像那些抛弃我的男人一样玩够了就走是高尚的?还是像你一样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我是高尚的?”
她走近一步,酒气喷在我脸上。“我告诉你什么是现实,雅人。现实是女人要在这个世界生存,就得利用自己有的东西。我有美貌,有身材,有让男人着迷的能力。我用这些换来了这家酒吧,换来了这个公寓,换来了你的学费和生活费。你觉得恶心?那就饿着肚子去上学,穿二手校服,放弃大学梦想,那样就纯洁了,高尚了,不恶心了!”
“所以你就卖?”我吐出这个词,像吐出毒液。
母亲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然后她抬起手,狠狠甩了我一耳光。
声音清脆响亮,在寂静的公寓里回荡。我的脸侧向一边,脸颊火辣辣地疼。
我们僵持着,呼吸粗重。沙发上,丽辉翻了个身,含糊地说了句梦话,又沉沉睡去。
许久,母亲放下手。她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颤抖。
“只是简单亲亲而已。”她突然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愣住了。
“他想要更多。”母亲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在夜店的卫生间里,他把我推进隔间,手伸进我衣服里。但我阻止了。我说不行,你还小,我是你朋友的母亲。他哭了,说他是认真的,说想和我在一起。我说等你长大了再说。”
她转过身,脸上没有表情。“所以,没有上床。只是一些吻,一些抚摸,一些让他觉得特别的小动作。仅此而已。三十五万买这些,对他来说很划算,不是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愤怒还在胸腔里燃烧,但某种更复杂的情绪正在滋生——是怜悯吗?还是更深的厌恶?
母亲弯腰捡起地上的高跟鞋,拎在手里。“我累了,去洗澡睡觉。你照顾他吧,沙发借他一晚。”
她走向浴室,在门口停下,没有回头。
“雅人,有一天你会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候我们都在灰色地带生存,用自己唯一拥有的方式。”
浴室门关上,水声响起。
我站在原地,脸颊还在刺痛。茶几上的奢侈品在月光下沉默地闪烁,像一场交易的证据。沙发上,丽辉在睡梦中微笑,可能正梦见他的“邻居姐姐”。
我走过去,看着他年轻的脸。酒精让他的脸颊泛红,嘴唇微张,眉头轻皱,像个不安的孩子。他的手机从口袋里滑出一半,屏幕还亮着,显示着Instagram的界面——最后一张照片,母亲穿着他的衬衫,眼神诱惑。
我拿起手机,关掉屏幕,放在茶几上。然后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
浴室的水声持续了很久。然后停止。脚步声经过我的门口,走进主卧。门关上的轻微咔哒声。
客厅里,丽辉的鼾声隐约传来。
我坐在地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脸颊上的疼痛逐渐消退,但心里的某个地方开始持续地、钝重地疼痛。
窗外,城市开始苏醒。凌晨三点的街道偶尔有车辆驶过,远处传来垃圾车的声音。天空从墨黑转向深蓝,第一缕晨光即将出现。
新的一天要开始了。但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彻底改变,无法回头。
我听见客厅传来动静,轻手轻脚地打开门缝。丽辉正在沙发上挣扎着坐起来,手按着额头,表情痛苦。他茫然地环顾四周,显然不记得自己在哪里。
然后他看见了茶几上的项链、香水、太阳镜。他愣住了,盯着那些东西,表情从困惑到回忆,再到一种复杂的醒悟。
浴室的方向传来母亲轻微的咳嗽声。丽辉转头望去,眼神变得柔软,嘴角不自觉地勾起。
我轻轻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但我知道,游戏还在继续。而筹码,已经不仅仅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