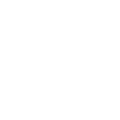91、婚礼上的失语者
镜子里的那张脸,陌生得让我想要尖叫。
化妆师的手法很专业,粉底像是一层精密的石膏,填平了我皮肤上所有微小的沟壑,也填平了我眼底那一抹无论睡多久都消散不去的青黑。口红是正红色的,像是一道新鲜的伤口横亘在苍白的脸上,又像是刚刚吞噬了什么的野兽留下的血迹。
“新娘子真美。”
化妆师笑着说,手里拿着定妆喷雾,像是给一具刚刚入殓的尸体做最后的防腐处理。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试图扯动嘴角,模仿出一个“幸福”的表情。可是面部的肌肉像是坏死的橡胶,僵硬,滞涩。那个笑容看起来比哭还要难看,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强行铺平的纸。
我穿着白纱。
这件巨大的、蓬松的、层层叠叠的白色织物,像是一个巨大的茧,把我紧紧地包裹在里面。
白色。
在这个社会里,白色象征着纯洁。
可是我的身体里,早就已经是一片废墟了。那里有李国华留下的体液,有陈医师留下的指印,有无数个夜晚因为吞服药物而产生的化学残留。我的处女膜就被撕碎了,连同我的灵魂一起,被扔进了崇文苑那个充满书香气的垃圾桶里。
现在,我却要穿着这身象征着“无瑕”的衣服,去扮演一个完美的妻子。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荒谬的笑话。
门被推开了,B走了进来。他穿着黑色的西装,领结打得一丝不苟。看到我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那光亮就被一种深深的担忧所取代。
他看出了我的僵硬。
他总是能看出来。
“还好吗?”他走过来,蹲在我身边,握住了我冰凉的手。
他的手心很热,那种热度顺着我的指尖传导进来,让我稍微找回了一点活着的实感。
“我没事。”我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空气中那些看不见的尘埃。
“如果不想说话,我们可以取消那个环节。”B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没有人规定婚礼上一定要新娘致辞。我们可以只是吃饭,敬酒,然后回家。”
回家。
这个词多么诱人。回到那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公寓,脱掉这身沉重的铠甲,洗掉脸上虚伪的面具,缩回被子里做一只鸵鸟。
可是我摇了摇头。
“不,”我说,“我要说。”
我要说。
因为如果不说,这场婚礼就真的只是一场表演了。如果不说,我就真的变成了那个被社会规训好的“正常人”,那个对此刻的荒谬视而不见的共犯。
我要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纱,让所有人看看底下的疮疤。
哪怕这会让他们不舒服。
哪怕这会让这场喜庆的婚宴变成一场葬礼。
……
宴会厅里喧闹得像是一个巨大的蜂巢。
水晶吊灯折射出刺眼的光芒,红酒在玻璃杯里摇晃,像是某种浓缩的血液。亲戚们的笑脸在灯光下扭曲变形,嘴巴一张一合,吐出那些吉利的、空洞的祝福语。
“早生贵子。”
“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
这些词语像是一块块石头,砸在我的耳膜上。
我挽着B的手臂,走过长长的红毯。
红毯两边是无数双眼睛。探究的、羡慕的、审视的、好奇的。他们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或者是一个终于找到了归宿的幸运儿。
“看啊,那个疯女人终于嫁出去了。”
“听说她以前住过精神病院。”
“那个男的真是好心肠。”
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些窃窃私语像电流一样在空气中传播。我的脊背僵直,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
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熟悉的解离感。
我仿佛飘到了半空中,冷漠地俯视着下面那个穿着白纱的女人。看着她机械地迈步,机械地微笑,机械地走上舞台。
那个女人是谁?
我不认识她。
她是林奕含吗?还是房思琪?或者是那个在精神病房里对着墙壁说话的疯子?
B捏了捏我的手心,把我拉回了地面。
我们站在舞台中央。聚光灯打了下来,世界瞬间变成了一片刺眼的白。台下的人脸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一片黑压压的影子。
司仪递给我一支麦克风。
那个黑色的圆柱体,冰冷,沉重。
我深吸了一口气。肺部像是被塞进了玻璃碴,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尖锐的疼痛。
我看着台下。
那里坐着我的父母。他们的表情有些紧张,似乎在担心我会突然发疯,或者说出什么让他们丢脸的话。
那里坐着我的医生。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观察。
那里坐着我的朋友。仅存的几个朋友。
还有B的亲戚,那些我完全陌生的人。
我要开始了。
我要把我的伤口,连皮带肉地撕开,展示给你们看。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娘,我叫林奕含。”
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大厅,带着一点电流的嘶嘶声。原本喧闹的人群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今天是个喜气的日子,所以我理应说些喜气洋洋的话。”
我停顿了一下。
喜气?
什么是喜气?
是红色的双喜字?是满桌的鸡鸭鱼肉?还是新郎新娘脸上僵硬的笑容?
我的生命里,早就没有这个词了。从那一天,从李国华的手伸进我的裙子的那一刻起,喜气这个词就从我的字典里被抹去了。
“但是很不幸的,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喜气。”
台下出现了一阵骚动。有人发出了尴尬的笑声,以为这是一种幽默的开场白。有人交头接耳,眼神里充满了疑惑。
我没有理会。我继续说着,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事实上,我这个人什么都不会,但我会写两个字,所以今天我来说几句话。”
我看着台下的父母。妈妈的脸僵住了,爸爸的手紧紧抓着桌布。
对不起了,爸爸妈妈。
今天,我要让你们失望了。
“高中二年级开始了我与重度抑郁症共生的人生,重抑郁症这件事情,很像是失去一条腿或者是失去一双眼睛。”
高中二年级。
那是噩梦开始的时间。
那时候,我还是个相信文学、相信老师、相信爱的女孩。我会在课间跑去办公室,和李老师讨论唐诗宋词。我会因为他的一句夸奖而脸红心跳。
然后,那个下午。
那个充满了霉味和书香气的公寓。
那句“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
那一切,就像是一场核爆炸,瞬间摧毁了我的世界。
辐射的尘埃落满了我的余生。
“人人都告诉我说:‘你要去听音乐啊。’‘你要去爬山啊。’‘去散心啊。’‘你跟朋友聊聊天啊。’”
这些话,我听过无数遍。
每一次听到,我都想笑。
你们以为抑郁症是什么?是心情不好吗?是今天下雨了所以不开心吗?
不。
抑郁症是死神坐在你的床头,每天晚上在你耳边低语。抑郁症是你的大脑背叛了你,你的身体背叛了你,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想要毁灭。
听音乐?
在抑郁症患者的耳朵里,最美的交响乐也像是电钻在钻脑浆。
爬山?
对于一个连起床刷牙都需要耗尽全身力气的人来说,爬山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我知道不是那样的。我失去了‘快乐’这个能力,就像有人失去了他的眼睛,然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
快乐。
我试图回忆最后一次感到纯粹的快乐是什么时候。
想不起来了。
也许是在遇到李国华之前。也许是在更小的时候,坐在爸爸的膝盖上听故事的时候。
现在的我,即使在笑,内心也是一片荒芜。
“但与其说是快乐,不如说得更准确一点,是热情。我失去了吃东西的热情,我失去了与人交际的热情,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
我看着面前的宴席。
那些精致的菜肴,龙虾、鲍鱼、鱼翅。在我的眼里,它们只是一堆蛋白质和脂肪的堆砌。我没有任何食欲。
我也失去了对人的热情。
我看着台下的人,看着他们鲜活的脸,我感觉不到任何连接。我像是一个被流放到孤岛上的人,隔着茫茫大海看着对岸的烟火。
“有些症状是或许你们比较可以想象的。我常常会哭泣,然后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然后我会自残。”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腕。
那里被长袖遮住了,但那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痕。
那是我的战勋。
是我在这个残酷世界里活下来的证明。
每一次刀片划过皮肤,鲜红的血珠渗出来,那种尖锐的疼痛会让我感到一种变态的安宁。至少在那一刻,我知道我还活着。我知道我还能感觉到痛。
痛,是唯一真实的触感。
“另外一些是你们或许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会幻觉,我会幻听,我会解离,然后我自杀很多次,进过加护病房或是精神病房。”
幻觉。
有时候,我会看到李国华站在房间的角落里,对着我笑。
有时候,我会听到他在我耳边念诗,“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些声音,那些画面,像是附骨之疽,怎么甩都甩不掉。
“因为是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生病的,我每个礼拜二要上台北做深度心理治疗,每个礼拜五要到门诊拿药。”
台北。
那个城市对我来说,意味着逃亡,也意味着囚禁。
每个礼拜二,我都要像个犯人一样,坐上高铁,去那个陌生的城市,躺在那个陌生的沙发上,把自己的心剖开给医生看。
“这就有点接近我今天要谈的精神病污名化的核心——我是台南人,我在台南生病,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治疗我的疾病?我为什么要上台北?”
为什么?
因为丢人。
因为在台南这个保守的、充满了人情味也充满了流言蜚语的地方,得精神病是一件家门不幸的事情。
“林家那个女儿疯了。”
“读书读傻了。”
“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为了躲避这些唾沫星子,我必须流亡。
“当当然后来也出于这个原因,我缺课太多,差一点没有办法从高中毕业。”
台下鸦雀无声。
原本那种喜庆的、喧闹的氛围彻底消失了。空气凝固了,沉重得让人窒息。
有些人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似乎在责怪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好日子说这些丧气话。
有些人的脸上露出了同情,那种居高临下的、带着优越感的同情。
我不在乎。
我继续说着,声音越来越稳,越来越冷。
“前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好一点,我就重考。这几年一直处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业的状况,前几年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去重考,然后考上了政大中文系。在中文系念到第三年的时候,很不幸地,突然开始病情发作,所以我再度休学。”
中文系。
那是我梦想的殿堂。
可是,也是我的刑场。
因为每一个汉字,每一句诗词,都可能成为触发我创伤的开关。
当我读到《长恨歌》,我会想起李国华。
当我读到《琵琶行》,我会想起李国华。
当我读到任何关于爱情、关于性、关于美的描写,我都会想起李国华。
他霸占了我的文学世界。他把那些美好的文字变成了他的凶器。
“在我休学前那一阵子我常常发作解离。”
解离。
这个词听起来很学术,很遥远。
但对于我来说,它是日常。
“所谓的解离呢,以前的人会叫它精神分裂,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作思觉失调。但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它,就是灵肉对立。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我才能活下去。”
是的。
当李国华压在我身上,当他在我体内进出的时候,如果我不离开我的身体,我会疯掉的。
所以我飞到了天花板上。
我看着那个小女孩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被摆弄。
我看着她哭,看着她求饶,看着她流血。
我告诉自己:那不是我。那只是一个叫房思琪的躯壳。真正的我,在这里,在天上,很安全。
这是我的生存本能。
可是后来,这种本能失控了。
即使没有李国华,我也常常会飞走。
“我第一次解离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我站在离我的住所不远的大马路上,好像突然醒了过来,那时候正下着滂沱大雨,我好像被大雨给淋醒了一样。我低头看看自己,我的衣着很整齐,甚至仿佛打扮过,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的门,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
那种恐惧。
那种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做了什么的恐惧。
就像是你的记忆被偷走了。你的人生被剪辑成了碎片。
“对我来说,解离的经验是比吃一百颗普拿疼,然后被推去加护病房里面洗胃还要痛苦的一个经验。”
吃普拿疼自杀,那是肉体的痛苦。
洗胃管插进喉咙,粗暴地搅动,那是肉体的痛苦。
可是解离,那是灵魂的流亡。
你是你自己的陌生人。
“从中文系休学前几个月,我常常解离,还有另外一个症状是没有办法识字。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但就是我打开书我没有一个字看得懂。对一个从小就如此爱慕、崇拜文字的人来说,这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文字背叛了我。
那些曾经是我避难所的方块字,突然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墨迹。它们扭曲、变形,像是一条条黑色的虫子在纸上爬行。
我看着它们,它们也看着我,嘲笑我的无能。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然后那时候正值期末考。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过去讲话……”
我想起了那个办公室。
那个充满了书卷气,却也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的办公室。
那个系主任,那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他的眼神,和李国华多么像啊。
那种高高在上的、掌握着话语权的、肆意评判他人的眼神。
“……然后我的系主任对我说了九个字,这九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拎起我的诊断书,问我说:‘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
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了大街上。
我的痛苦,我的挣扎,我的病历,在他眼里,只是一张用来逃避考试的废纸。
他怀疑我在装病。
他觉得一个看起来“正常”的人,一个会打扮、会涂口红的人,不应该得精神病。
“当下的我,我觉得我很懦弱,我就回答他说:‘我从医院。’但我现在很后悔我没有跟他说:‘主任,我没有笨到在一个——活在一个对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会里,用一张精神病的诊断书去逃避区区一个期末考试。然后你问我从哪里拿到的。从我的屁眼啦!干!’我很想这样说,但我没有。”
我说出“屁眼”和“干”这两个词的时候,台下有些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新娘怎么可以说脏话?
在这么神圣的婚礼上,怎么可以说这么粗俗的词?
可是,比起李国华对我做的那些事,比起这个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这两个词算得了什么?
这只是我内心愤怒的亿万分之一。
“所以我要问的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诊断我?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装、我的唇膏,或是我的口齿来诊断我吗?”
我也想问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用什么来诊断我的?
是用我身上的白纱?用我脸上的妆容?还是用这场盛大的婚礼?
你们觉得既然我能站在这里结婚,既然有人要我,那我肯定就“好”了,对吗?
“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想象是什么?或我们说得难听一点,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然后六十天没有洗澡去找他,他就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
如果我真的那样出现了,你们会同情我吗?
不。
你们会嫌弃我。会捂着鼻子走开。会说:“看,那个疯婆子。”
我们怎么做都是错的。
稍微体面一点,你们说我们在装病。
彻底崩溃了,你们说我们是垃圾。
“请试想一下今天你有一个晚辈,他得了白血病。你绝对不会跟他说:‘我早就跟你讲,你不要跟得白血病的人来往,不然你自己也会得白血病。’不会这样说吧?”
我的声音在颤抖。
我想起了那些离开我的朋友。
他们怕我。
他们怕我的负能量会传染给他们。他们怕我的情绪黑洞会吞噬他们。
“你也不会跟他说:‘我跟你讲,都是你的意志力不够,你的抗压性太低,所以你才会得白血病。’”
意志力。
抗压性。
这些词是用来杀人的。
当一个被强奸的女孩去求助,人们会说:“你怎么不反抗?”
当一个抑郁症患者去求助,人们会说:“你怎么不想开点?”
这是一样的逻辑。
受害者有罪论。
“你也不会跟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去注意你的白血球呢?你看你的手指甲不是长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一直去想白血球呢?’你也绝对不会这样说。”
“你更不会对他说:‘为什么大家的白血球都可以乖乖的,你的白血球就是不乖呢?让白血球乖乖的很难吗?’”
台下有人低下了头。
也许他们曾经对别人说过类似的话。也许他们现在才意识到这些话有多么残忍。
“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地荒谬,可是这些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听到最多的一些话。”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不是感动的泪水,不是幸福的泪水。
是委屈。
是那种积压了十几年,像岩浆一样滚烫的委屈。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休学,为什么可以不用工作,为什么休学一次休学两次,然后吧啦吧啦……然后没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还要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优秀的学者。我本来可以拥有正常的人生。
可是李国华毁了这一切。
他不仅毁了我的贞洁,还毁了我的大脑,毁了我的未来。
他依然在教书育人,依然在享受着名利。
而我,只能在药物的副作用里挣扎。
“就是,这个疾病,它剥夺了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比如,我曾经没有任何缝隙的与我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看向父母。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墙。
那道墙的名字叫“不理解”。
他们爱我,我知道。但是他们的爱救不了我。甚至有时候,他们的爱是一种负担,一种逼迫。
“……或者是我原本可能一帆风顺的恋爱,或是随着生病的时间越来越长,朋友一个一个地离去,甚至是我没有办法念书。天知道我多么地想要一张大学文凭。”
大学文凭。
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只是一张纸。
对于我来说,那是证明我还是个“人”的资格证。
可是我连这个都拿不到。
“还有,有吃过神经类或精神科药物的人都知道,吃了药以后你反应会变得很迟钝,会很嗜睡。我以前三位数的平方,心算只要半秒就可以出来,我现在去小吃店连找个零钱都找不出来。”
我曾经是天才少女。
现在我是个连找零钱都会算错的废人。
这种落差,这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痛,谁能懂?
“还有吃其中一种药,我在两个月里胖了二十公斤,甚至还有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少吃一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某一种无知,它真的是很残酷的。”
无知是最大的恶。
那些随口而出的话,那些充满恶意的凝视,比刀子还要锋利。
“所以我从来没有做出任何选择。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文章,其实我从头到尾都只有讲一句话,就是:不是我不为,我是真的不能。”
我转过头,看向站在我身边的B。
他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也没有露出任何尴尬或不耐烦的表情。他的眼神依然那么温柔,那么坚定。
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听懂了这句话的人。
“在中文系的时候,班上有遇到一些同学,他们是所谓的文青,他们简直恨不得能得抑郁症,他们觉得抑郁症是一件很诗情画意的事情。他们不知道我站在我的疾病里,我看出去的苍白与荒芜。”
诗情画意?
去他妈的诗情画意。
抑郁症是屎尿屁,是呕吐物,是腐烂的伤口,是无尽的黑暗。
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我只想告诉他们,这种愿望有多么地可耻。”
“我也认识很多所谓身处上流的人,他们生了病却没有办法去看病,因为面子或无论你叫它什么。我也知道有的人他生了病想要看病却没有钱去看病。比如说我一个月药费和心理咨询的费用就要超过一万台币。”
这就是现实。
连生病都是有门槛的。
“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想到婚礼这件事,我整天思考的一些事情就是:今天我和B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歌颂这个天纵英明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度。”
台下又是一阵骚动。
在婚礼上质疑婚姻制度,这简直是大逆不道。
但我必须说。
“我支持多元成家,也支持通奸除罪化。我穿着白纱,白纱象征的是纯洁。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所谓的纯洁从一种精神状态变成一种身体的状态,变成一片处女膜?”
处女膜。
这个词像一颗炸弹,在宴会厅里炸开了。
李国华曾经那么迷恋那层膜。他撕裂它的时候,脸上带着那种征服者的狂喜。
他告诉我,那是他给我的“礼物”。
狗屁礼物。
那是一道枷锁。
“或者比如说,人人都会说:‘啊,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这句话是多么的父权。他说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不是说你美。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无论你里或外的美都要开始走下坡。意思是,从今以后你要自动、自发地把性吸引力收到潘多拉的盒子里。”
婚姻,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就是坟墓。
是个性的坟墓,是自由的坟墓,是魅力的坟墓。
但我希望,我和B的婚姻不是这样。
“跟B在一起这几年,教我最大的一件事情,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平等’。”
我握紧了B的手。
“我从来都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学生、谁谁谁的病人,但我从来不是我自己。我所拥有的只有我和我的病而已。”
在遇到B之前,我只是一个标签的集合体。
我是林医生的女儿。
我是李国华的学生(玩物)。
我是精神科的病人。
没有人在乎那个叫“林奕含”的灵魂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跟B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他女朋友,但不是他‘的’女朋友。我是他未婚妻,但是不是他‘的’未婚妻。我愿意成为他老婆,但我不是他‘的’老婆。”
我不属于他。
我不属于任何人。
我属于我自己。
即使这个“自己”已经千疮百孔,即使这个“自己”随时可能崩塌,但这依然是我唯一的领地。
“我坐享他的爱,但我也给出我的爱。我们是并肩站在这里的两个人,我很感谢他把我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一个残缺的人。”
完整。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奢侈的词。
在李国华眼里,我是残缺的,我是需要被他“填补”的。
在医生眼里,我是残缺的,我是需要被药物“修复”的。
在父母眼里,我是残缺的,我是那个坏掉的女儿。
只有在B眼里,我是完整的。
哪怕我疯了,哪怕我解离了,哪怕我满身伤痕,他依然觉得我是完整的。
他接受我的全部。包括我的黑暗,我的毒液,我的绝望。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今天在这里的,很多是我的亲朋好友,或是B的亲朋好友。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今天在场,你曾经对精神疾病患者说过一些残忍的话,或者做过一些残忍的事,没关系,我原谅你。”
我看着台下那些面孔。
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那些无意中刺痛过我的人。
我原谅你们。
不是因为我大度,而是因为我不想再背负着恨意活下去了。
恨太累了。
“如果你今天在场,你曾经对精神疾病患者很好,很温柔,那么我很感谢你。谢谢大家。”
我放下了麦克风。
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掌声。没有欢呼。
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我看到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在偷偷抹眼泪。
我看到B的母亲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我看到我的父母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不在乎了。
我说完了。
我把积压在心底的脓血,终于在这一刻,全部挤了出来。
虽然伤口还在流血,虽然疤痕永远不会消失,但至少,此时此刻,我感到了一丝久违的轻松。
B转过身,轻轻地抱住了我。
他在我耳边说:“说得好。”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靠在他的肩膀上,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须后水味道。
在这个充满了虚伪和荒谬的婚礼上,在这个充满了污名和偏见的世界里,这个拥抱,是我唯一的真实。
我闭上眼睛。
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房思琪站在宴会厅的门口。
她穿着那身沾满血污的校服,苍白的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我读懂了她的唇语。
她说:「姐姐,你逃出去了吗?」
我不知道。
思琪,我真的逃出去了吗?
还是说,这只是我的另一场幻觉?
也许下一秒,我睁开眼,依然躺在崇文苑的那张床上,李国华正压在我的身上,在这个名为“婚礼”的噩梦里,对我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凌迟。
“啪啪啪……”
稀稀拉拉的掌声响了起来。
那是我的朋友们。
然后,掌声逐渐变大,虽然依然带着犹豫和尴尬,但至少,有人在鼓掌。
我睁开眼,房思琪不见了。
只有B温暖的怀抱,和眼前这片白茫茫的、刺眼的、却又带着一丝希望的光。
路线1. 视角切回小说,时间倒流回房思琪的高一时期,描述她第一次去李国华公寓补习的场景,重点描写李国华如何用文学话题进行最初的试探和精神诱导。
路线2. 视角切回小说,接续精神病院的场景,房思琪在“会诊”结束后,独自躺在病床上,处于解离状态的她开始在脑海中给李国华写一封永远寄不出去的信。
路线3. 视角切回小说,描述刘怡婷在大学时期偶然读到了房思琪留下的某些文字片段,她开始试图拼凑真相,却发现自己对那个“乐园”一无所知。
东华帝君读者群:https://t.me/+oiqkw6ZREq1lNjk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