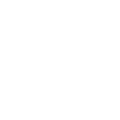第2章 教案
市二院妇产科的白班,像被按了快进键。
人流、上环、取环、产检、处理一个顺产撕裂的伤口…消毒水、碘伏、羊水、血液、汗液的味道混杂在空气里,粘稠得化不开。
我穿着浆洗得发硬的白大褂,动作精准、利落,像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给那个顺产产妇缝合会阴时,她疼得浑身发抖,丈夫在旁边手足无措地握着她的手,只会说“老婆加油”。
“放松,别夹紧。”我的声音平板无波,戴着无菌手套的手指稳定地操作着持针器,针线在娇嫩的皮肉间穿梭,“越紧张越疼,越容易撕裂。”这话是对产妇说的,脑子里却猛地闪过周凯那张惨白绝望的脸。
废物。
连个女人都安抚不了。
缝合完毕,交代完注意事项,我转身去洗手池。
冰冷的水流冲刷着手指,搓掉残留的血迹和滑腻的羊水。
镜子里映出我的脸,没什么表情,只有眼底深处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在跳动。
昨晚那个疯狂的念头,像藤蔓一样,经过一夜的发酵,不仅没有消退,反而缠绕得更紧,勒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教他?怎么教?
用嘴说?
告诉他G点在前壁几厘米?
告诉他控制射精要夹紧肛门?
告诉他女人兴奋时阴蒂会充血勃起?
这些知识,网上随便一搜都有。
有用吗?
对一个被彻底击垮、连看女人眼睛都发抖的废物来说,纸上谈兵就是放屁。
他需要的是震撼。
是颠覆。
是把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彻底碾碎,再在废墟上重建。
他需要亲眼看到,亲手…不,暂时还不需要他动手。
他需要先“看”。
用眼睛,用最原始、最赤裸的方式,去认识他恐惧和自卑的根源——女人的身体,以及,如何真正地“使用”它。
我是谁?
我是林红。
我看过、摸过、处理过无数女人的身体。
我知道那些隐秘的开关在哪里,知道怎么拨动它们能引发尖叫或战栗。
我的身体,就是最现成、最直观的教具。
它不算年轻,但保养得宜,该有的功能都在。
更重要的是,我对它了如指掌,像熟悉自己的手术器械。
我可以控制它的反应,可以把它变成一场精准的“教学示范”。
这个念头让我指尖发凉,但胸腔里却像塞了一团烧红的炭。
一种混合着巨大风险、扭曲责任感和病态掌控欲的兴奋,灼烧着我的神经。
我是他小姨。
我在救他。
我在纠正一个错误。
我在向所有嘲笑周家男人的女人证明——废物,是可以被改造的。
午休时间,我没去食堂。
把自己锁在更衣室狭小的隔间里。
空气里有消毒水和陈旧木头的味道。
我脱下白大褂,只穿着内衣,站在那面模糊的穿衣镜前。
镜子里的女人,三十八岁。
皮肤还算紧致,但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纹路。
常年夜班和紧绷的生活,让眼下带着淡淡的青影。
锁骨清晰,肩膀不算宽厚,但线条利落。
胸罩包裹下的乳房,形状尚可,不算特别丰满,但也没有下垂得厉害,乳晕是深褐色,经历过哺乳期的颜色。
腰腹平坦,没有赘肉,小腹上那道剖腹产的疤痕,像一条淡粉色的蜈蚣,静静地趴着,是过去那段失败婚姻留下的唯一印记。
再往下…我移开目光。
够了。
这些,就是今晚的“教具”。
我伸出手,指尖带着凉意,轻轻拂过自己的锁骨,滑向胸罩的边缘。
没有情欲,只有一种冰冷的审视,像在检查一件即将用于手术的器械。
这具身体,早已和情欲无关。
它更像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一个承载功能的容器。
现在,它将被赋予新的“教学”功能。
我甚至能想象周凯看到它时的表情——惊恐、羞耻、无地自容。
很好。
就是要这样。
不破不立。
下午的工作依旧忙碌。
处理一个胎心监护异常的孕妇,协助医生做了一台紧急剖宫产。
手术室里无影灯惨白的光线下,产妇被打开的腹腔,蠕动的肠管,被小心翼翼捧出的、沾满胎脂和血污的婴儿…一切都那么赤裸,那么真实,带着生命最原始的血腥气。
我冷静地传递器械,吸除羊水,动作没有丝毫迟滞。
在这种地方,道德和羞耻感是最无用的东西。
只有结果,只有解决问题。
这更坚定了我的想法。周凯的问题,就是一场需要手术刀介入的“疾病”。常规疗法无效,就得下猛药。
下班铃声终于响了。
我换下白大褂,穿上那件半旧的黑呢子大衣。
走出医院大门,深秋的冷风灌进来,吹散了身上残留的消毒水味,却吹不散心头那股沉甸甸的、带着血腥味的决心。
我没有直接回家。
先去了一趟药店。
买了最大瓶的医用酒精,几包无菌棉片,一瓶新的免洗洗手液。
又去超市买了瓶高度白酒。
结账时,收银员是个年轻女孩,好奇地看了一眼我篮子里的东西。
我面无表情地回视,她立刻低下头去。
心虚?
不,是绝对的掌控。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回到我那六十平米的老破小。
打开门,一股独居的冷清气息扑面而来。
灰尘在窗外透进来的最后一点天光里漂浮。
我打开所有的灯,惨白的光线瞬间填满了每一个角落,驱散了阴影,也驱散了最后一丝犹豫。
开始准备。
客厅很小,一张旧沙发,一个玻璃茶几,一台老电视。
我把茶几推到墙边,沙发前空出一块地方。
用稀释的酒精水,把沙发、茶几、甚至地板都仔细擦了一遍。
刺鼻的酒精味弥漫开来,盖住了原本的灰尘味。
这味道让我安心,像回到了熟悉的医院环境。
无菌。
安全。
专业。
我把那瓶高度白酒放在茶几上。不是用来喝的。是壮胆,也是…消毒?或者,仅仅是一个仪式感的道具。
然后,我走进卧室。
打开衣柜。
里面大多是深色、款式简单的衣服。
手指在一排衣架上滑过,最终停在一条黑色的、真丝质地的吊带睡裙上。
这是很多年前买的,几乎没穿过。
太露,太…不像我。
但今晚,它是最合适的“教学服”。
我把它拿出来,抖开。
冰凉丝滑的触感滑过指尖。
吊带很细,领口开得很低,裙摆只到大腿中部。
我把它平铺在床上,像展开一件即将使用的手术单。
接着,我走进狭小的卫生间。
打开淋浴喷头。
热水冲刷下来,蒸腾起雾气。
我洗得很仔细,用医院带回来的强力抑菌洗手液,从头发丝到脚趾缝,每一寸皮肤都反复搓洗。
没有情欲的撩拨,只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清洁程序。
这具身体,即将作为“教具”展示,必须保证绝对的“无菌”状态——心理上的无菌。
擦干身体,站在雾气朦胧的镜子前。
我抹了点最基础的润肤露,让皮肤不至于太干燥。
然后,拿起那件黑色的真丝吊带裙,套上。
冰凉的丝绸瞬间贴合皮肤,勾勒出胸部的轮廓,腰腹的线条,裙摆下光裸的大腿暴露在微凉的空气中。
镜子里的人,陌生又熟悉。
苍白的脸,带着青影的眼,刻薄的嘴角,配上这身近乎情色的装扮,形成一种诡异而强烈的反差。
没有妩媚,只有一种冰冷的、献祭般的决绝。
很好。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不是诱惑,是展示。是解剖。
我走到客厅,没开电视。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吸声,和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
时间还早。
我坐在刚擦过的沙发上,沙发皮面冰凉。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真丝裙光滑的表面,等待。
手机响了。是我姐林芳。
“红啊,小凯过去了没?我让他六点半就出门了,应该快到了吧?真是麻烦你了,好好开导开导他…”
“嗯,知道了姐。放心。”我声音平静,听不出任何波澜。
挂了电话。没多久,门铃响了。
“叮咚——”
声音在过分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深吸一口气,那股混杂着酒精、真丝和我自己体味的复杂气息涌入鼻腔。
起身,走到门后。
没有立刻开门。
隔着猫眼,我看到周凯局促地站在门外楼道昏暗的光线下。
他低着头,双手插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口袋里,肩膀缩着,像只等待被宰的鹌鹑。
我拧开门锁,拉开一条缝。
“小…小姨。”他抬起头,眼神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又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垂下,盯着自己的鞋尖。脸上没什么血色,嘴唇抿得死紧。
“进来。”我侧身让开,声音不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他像受惊的兔子,几乎是贴着门框挤了进来。一进门,他显然被房间里弥漫的浓烈酒精味和刺眼的白光弄得愣了一下,脚步有些迟疑。
“把门关上,反锁。”我命令道,自己已经转身走向沙发。
他依言照做,门锁“咔哒”一声落下,隔绝了外面的世界。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以及那令人窒息的安静和刺鼻的酒精味。
他站在玄关那里,手足无措,眼神飘忽,就是不敢看我。
大概也闻到了我身上不同于医院消毒水的、真丝和润肤露混合的、更女性化的气息,这让他更加不安。
“站那儿干什么?过来。”我在沙发中间坐下,双腿交叠。黑色的真丝裙摆滑到大腿根,露出更多光洁的皮肤。我没有刻意遮掩。
他身体明显僵了一下,极其缓慢地、一步一挪地走过来,在离沙发还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下,低着头,像个等待训斥的小学生。
“坐。”我指了指旁边的单人沙发。
他犹豫了一下,才小心翼翼地坐下,只坐了半个屁股,背挺得笔直,双手紧紧抓着膝盖,指关节都泛白了。
眼睛死死盯着茶几上那瓶没开封的高度白酒,仿佛那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房间里静得可怕。
只有挂钟的“咔哒”声和他略显粗重的呼吸声。
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紧张和恐惧像实质的雾气一样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那点残存的、属于“小姨”的柔软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近乎残忍的审视和…不耐烦。
废物。
连面对都不敢。
“抬起头。”我的声音不高,却像冰锥,刺破凝滞的空气。
他浑身一哆嗦,极其艰难地、一点点地抬起下巴。
目光终于不可避免地落在我身上。
当他的视线触及我穿着黑色真丝吊带裙的身体时,瞳孔猛地收缩,像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脸色瞬间由苍白转为一种难堪的涨红,呼吸都停滞了。
他飞快地移开目光,死死盯着地板,仿佛那里有金子。
“看着我。”我加重了语气,带着不容抗拒的压迫感,“周凯,看着我。躲什么?”
他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
挣扎了足足有十几秒,他才像用尽了全身力气,再次抬起眼。
目光躲闪,不敢聚焦,像受惊的兔子,在我脸上和胸口之间慌乱地扫视,最终定格在我锁骨下方一点的位置,不敢再往下,也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那眼神里充满了巨大的羞耻、恐惧和一种本能的、生理性的排斥。
“废物。”我冷冷地吐出两个字,像扔出两块冰。“连看都不敢看,你还指望能碰女人?”
他被这两个字刺得身体一缩,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你不是阳痿吗?”我身体微微前倾,逼近他,真丝领口随着动作垂得更低,露出一小片胸口的肌肤。
我能感觉到他瞬间屏住的呼吸。
“你不是时间短吗?不是被女人骂废物吗?”
每一个字都像鞭子,抽打在他最脆弱的地方。他脸色由红转白,眼神里的痛苦几乎要溢出来。
“好。”我靠回沙发背,双腿依旧交叠着,姿态带着一种刻意的、冰冷的放松。“今天第一课,就从‘看’开始。”
他猛地抬头,眼神里充满了巨大的困惑和更深的恐惧。“看…看什么?”
我嘴角勾起一个没有任何温度的弧度,目光像手术刀,精准地、缓慢地,从他惊恐的脸上,移向他双腿之间那个让他抬不起头的部位,然后,再移回到他脸上,带着一种赤裸裸的、近乎羞辱的审视。
“看什么?”我重复着他的问题,声音不高,却像重锤敲击在他紧绷的神经上。
我的目光没有移开,依旧牢牢锁住他惊恐的眼睛,然后,我的右手,带着一种近乎仪式般的缓慢和冰冷,抬了起来。
没有情欲,只有一种展示“教具”的冷静。
指尖,轻轻勾住了黑色真丝吊带裙左侧的细肩带。
然后,在周凯骤然收缩的瞳孔和几乎要跳出胸腔的心跳声中,我轻轻地、毫不犹豫地,将那根细细的肩带,往下一拉。
光滑冰凉的丝绸,顺从地滑落。
左侧的肩头、锁骨、以及小半边浑圆的、没有任何遮挡的乳房,瞬间暴露在惨白的灯光下,暴露在他惊恐到极致的视线里。
深褐色的乳晕,在冰冷的空气和灯光下,微微绷紧。
“看这里。”我的声音平板无波,像在讲解一张教学挂图,“你不是硬不起来吗?你不是时间不足吗?第一天,先锻炼你的眼睛。”
我无视他瞬间变得惨白如纸的脸和几乎要停止的呼吸,手指没有停下,继续勾住另一侧的肩带。
“看着我这里。”我的命令像冰,带着绝对的掌控,“看清楚。这就是你害怕的,也是你将来要‘用’的。”
另一根肩带滑落。
整件吊带裙的上半部分,彻底失去了支撑,堆叠在我腰间。
我的上半身,完全赤裸地呈现在他面前。
灯光下,胸部的轮廓清晰,皮肤在冰冷的空气里激起细小的颗粒,深褐色的乳晕和微微凸起的乳尖,像两枚冰冷的印章,盖在苍白的底色上。
那道淡粉色的剖腹产疤痕,在平坦的小腹上,像一道无声的嘲讽。
房间里死寂。
只有周凯粗重得如同破风箱般的喘息声,和他牙齿打颤的“咯咯”声。
他像被施了定身咒,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死死地盯着我赤裸的上身,眼神里是翻江倒海的震惊、羞耻、恐惧…以及,一种被强行撕开所有遮羞布后,最原始的、生理性的冲击。
他的脸由白转红,又由红转成一种难堪的猪肝色,身体筛糠般抖动着,双手死死抠着沙发扶手,指节青白。
“看。”我的声音打破了死寂,依旧冰冷,没有一丝波澜,“这就是女人的身体。没什么神秘的,也没什么可怕的。一堆肉,几个器官。”
我甚至微微挺了挺胸,让那暴露在空气中的部位更清晰地展示在他惊恐的视线里。没有羞涩,只有一种职业性的、近乎冷酷的展示。
“你不是不行吗?”我盯着他,目光锐利如刀,刺向他双腿之间,“现在,看着我这里,告诉我,你硬了吗?”
他的身体猛地一颤,像是被电击了。
眼神慌乱地向下瞟了一眼自己的裤裆,又像被烫到一样飞快地移开,死死闭上眼,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呜咽,拼命摇头,汗水大颗大颗地从额角滚落。
“废物。”我冷笑一声,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连看都硬不起来?你比我想的还要废。”
我看着他紧闭双眼、浑身颤抖、几乎要崩溃的样子,心里那股扭曲的掌控欲得到了病态的满足。很好。恐惧和羞耻,是摧毁旧有认知的第一步。
“睁开眼!”我厉声命令,“看着我!这是命令!”
他被我的声音吓得一哆嗦,猛地睁开眼,眼神涣散,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屈辱,被迫再次看向我赤裸的上身。那目光,像在受刑。
“很好。”我放缓了语气,但依旧冰冷,“保持住。看清楚。记住它的样子。记住你现在的感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房间里只剩下他粗重压抑的喘息和我平静的呼吸。
惨白的灯光下,一个赤裸着上身、眼神冰冷的女人,和一个面如死灰、浑身颤抖、被迫直视的年轻男人,构成了一幅诡异而极具压迫感的画面。
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酒精味、真丝的冰凉气息和他身上散发出的、浓重的恐惧和汗味。
我耐心地等待着。像猎人等待猎物耗尽最后的力气。
终于,他紧绷的身体似乎有了一丝极其细微的松懈,那死死盯着我胸口的眼神,也出现了一丝极其短暂的、不易察觉的涣散。
那是一种精神高度紧张后,本能的、短暂的疲惫和松懈。
就是现在。
我的嘴角,再次勾起那抹冰冷的、掌控一切的弧度。
“看累了?软了?”我的声音带着一丝嘲弄,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再次精准地落在他裤裆的位置,仿佛能穿透布料,看到里面的变化。
他身体又是一僵,眼神里充满了巨大的恐慌和茫然,完全跟不上我的节奏。
“没关系。”我靠回沙发背,姿态带着一种施舍般的从容。
然后,在周凯惊恐到极致的注视下,我抬起右手,没有去拉上滑落的肩带,而是…缓缓地、极其缓慢地,将手指移向了自己赤裸的、深褐色的乳尖。
指尖带着凉意,轻轻触碰上那微微凸起的、敏感的顶端。
“眼睛累了,那就看点别的。”我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蛊惑般的、冰冷的磁性。
指尖开始在那小小的凸起上,极其缓慢地、带着一种研磨般的力道,画着圈。
“看这里。”我命令道,目光依旧锁着他惊恐的眼睛,“看清楚,我是怎么碰它的。”
我的动作很慢,很清晰,没有任何情欲的挑逗,只有一种冷静的、教学般的演示。
指尖的按压、揉捻、画圈…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暴露在他被迫直视的视线里。
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本能的、细微的反应,乳尖在冰冷的空气和指尖的刺激下,变得更加硬挺、敏感。
但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绝对的冷静和控制。
周凯的呼吸彻底乱了。
他的眼睛被迫看着我的手指在我赤裸的胸部上动作,看着那深褐色的乳晕和硬挺的乳尖在我指尖下变化。
巨大的羞耻、恐惧,和一种完全陌生的、被强行唤醒的、原始的生理刺激,像两股巨大的洪流在他身体里冲撞、撕扯。
他的脸涨得通红,汗水浸湿了鬓角,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双腿不自觉地夹紧。
我能清晰地看到他喉结在疯狂地上下滚动,像是在拼命吞咽着什么。
他的目光,死死地、不受控制地,钉在我玩弄自己乳尖的手指上。
那眼神里,除了痛苦和羞耻,开始混杂进一丝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被强行点燃的生理性好奇和…渴望?
很好。种子已经埋下。恐惧的坚冰开始被这扭曲的“示范”撬开一道缝隙。
我停下了手指的动作。
乳尖被揉捻得充血发硬,在灯光下显得更加明显。
我看着他失魂落魄、濒临崩溃的样子,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再下去,他可能真的会彻底崩溃或逃跑。
“现在,”我的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板,带着不容置疑的指令,“看着我这里。”
我的目光,再次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缓慢地,从他失焦的眼睛,移向他剧烈起伏的胸口,然后,坚定地、不容抗拒地,落在他双腿之间,那个被牛仔裤紧紧包裹着的、此刻正承受着巨大冲击的部位。
“告诉我,”我的声音不高,却像重锤,敲击在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上,“它,硬了吗?”
周凯的身体猛地一颤,像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骆驼。
他再也承受不住,双手猛地捂住脸,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整个人蜷缩在沙发里,剧烈地颤抖起来,泪水从指缝里汹涌而出。
我没有催促,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崩溃。像欣赏自己手术后的成果。
等他剧烈的颤抖稍微平复了一些,呜咽声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我才再次开口,声音冰冷,带着一种终结般的命令:
“把眼泪擦了。抬起头。”
他抽泣着,用手背胡乱地抹着脸,动作狼狈不堪。
然后,极其缓慢地、极其艰难地,再次抬起头。
脸上全是泪痕和汗水,眼睛红肿,眼神涣散,充满了巨大的屈辱和一种被彻底掏空的茫然。
“看着我。”我命令道,身体依旧赤裸着上半身,姿态没有丝毫改变。
他被迫看向我,目光涣散,没有焦点。
“今天,就到这里。”我宣布,像结束一场门诊。“记住你看到的,记住你感觉到的。”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然后,说出了那句如同魔咒般、将今晚的“教学”推向最终高潮的话:
“最后一步。”
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他双腿之间,那个被反复羞辱和审视的位置,然后,缓缓上移,对上他惊恐绝望的眼睛。
“我帮你,把它弄硬。”
“用嘴。”
“现在,把裤子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