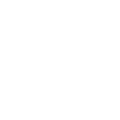第56章
直到某日,转折来得猝不及防,却又像是命中注定。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天色灰暗,愁云惨淡。
出远门多日的李冉回来了。
向来注重仪表,将“君子正衣冠”挂在嘴边,连一丝褶皱都不能容忍的儒圣大人,此刻却形同鬼魅,狼狈不堪。
那件曾经象征着清贵与威严的月白色儒衫如今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破破烂烂地挂在他身上,满是泥泞和早已干涸发黑的血污,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他的右腿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显然是断了,每拖行一步,都牵动着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额头上渗出豆大的冷汗。
那顶象征着他身份地位的儒冠也不知所踪,平日里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发髻此刻散乱打结,蓬头垢面,如同一个从熊洞中侥幸逃脱的疯癫乞丐。
他双目赤红,布满血丝,眼神中不再是往日的温文尔雅与故作高深,而是充满了怨毒、憎恨,以及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后怕。
他受了很重的伤,仿佛刚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浑身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暴戾气息,那股混杂着血腥、泥土和腐败的恶臭,让习惯了清雅熏香的甄府都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但甄海瑶只是冷冷地瞥了一眼,旋即便收回了目光,没有去问,也不想去问。
这两百年来毫无温度的婚姻,早已让她学会了对他的一切漠不关心,冷眼相待。
李冉也没有理会她的目光,甚至没有看她一眼,便一瘸一跛地将自己关进了书房。
哐当一声巨响,是门闩落下的声音,沉重得像一口棺材的盖子合上。
他反锁了门,整整一月,不见天日,不饮不食。
“混账!该死……该死!”
“老匹夫!”
“……符……阴我!……卑鄙!无耻!”
“……你枉为圣……啊啊啊啊——!!”
甄海瑶偶尔路过书房,总能听到里面传来器物被狂怒砸碎的巨响,以及他如同败犬般歇斯底里的暴怒嘶吼和恶毒咒骂。
那些曾经用来书写道德文章的珍贵砚台,那些被他视若珍宝的前贤法帖,那些千金难求的孤本字画,此刻都成了他发泄无能狂怒的牺牲品。
她站在门外,静静地听着,心中竟没有丝毫波澜,只觉得陌生而滑稽,又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感到罪恶的隐秘的快意。
那个高高在上的圣人,那个永远用道德和规矩将她牢牢束缚的伪君子,终于也露出了他最丑陋、最真实的一面。
一个月后,书房的门终于开了。
当李冉走出房门时,人已经憔悴脱相,干瘦阴沉,眼窝深陷。
他身上的伤势似乎已经用法力强行压制住,又恢复了往日那副衣冠楚楚的模样,但他的眼神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阴鸷和疯狂,那是一种输光了所有赌注的赌徒才会有的眼神,让甄海瑶感到一阵发自骨髓的寒意。
而李冉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便如同最锋利的刀斧,将她心中对他仅存的那一丝作为“家人”的淡漠情分,以及对这个男人最后一丝可笑的幻想,也彻底斩断碾碎。
李冉那双泛着诡异绿光的眼睛死死盯着她,仿佛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
“海瑶,丞相大人对你的才情与美貌素来欣赏,你……收拾一下,去丞相府住上一段时日吧。”
他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平静,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那一瞬间,甄海瑶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愣在原地,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张保养得宜总是带着淡淡疏离美感的美丽面容上,血色褪尽,变得惨白如纸。
她张了张嘴,喉咙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干涩发紧,胸口闷得发慌,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李冉似乎对她的反应早有预料,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她的反应。
“这对我的仕途,对我们甄家,都有莫大的好处。”
他面无表情,自顾自地接着说道,那张因消瘦而显得颧骨高耸的脸上,竟然挤出了一丝虚伪的循循善诱的“温和”:
“只要我能借此机会加官进爵,获得更多的声望和支持,届时人道气运反哺,我的儒道修为便可稳固,甚至更进一步!”
“你身为我的妻子,理应为我分忧,为家族大业牺牲。放心,事成之后,我必不会亏待于你。将来……”
后面的话,甄海瑶已经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
她只觉得天旋地转,耳边嗡嗡作响,她的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崩塌破碎。
她的骄傲,她的优雅,她过去两百年所坚守的一切,她作为人、作为女人的最后一丝尊严,都被这个男人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踩碎,碾烂,践踏成泥。
他竟然卖妻求荣?!
这个男人,她的丈夫,被天下学子奉为圭臬的儒家圣人,为了攀附权贵,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弥补受损的修为,竟然要将她,将自己的妻子,当作一件可以随意赠送用来换取前程的礼物,亲手送到另一个男人的床榻上去?!
他怎么会?!
他怎么敢?!
这是何等的卑劣!何等的无耻!何等的下作!!
恶心感从胃里直冲喉咙,让她几欲作呕。
“李冉!你这个畜生——!!”
甄海瑶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声嘶力竭地怒斥,那声音凄厉悲伤,好似杜鹃啼血。
她气得浑身发抖,端庄优雅的淑女涵养在这一刻荡然无存。
“妇人之见!愚不可及!”
李冉那张曾经还算儒雅的脸庞瞬间变得狰狞扭曲,他终于撕下了那张戴了百年的伪善面具,露出了底下最真实丑陋的腐肉。
“这是为了我们甄、李两家的荣耀!是为了我的大道前途!也是你作为妻子应尽的本分!你……”
“住口!”
积压了多年的怨恨与屈辱,在这一刻尽数爆发。
甄海瑶厉声怒喝,满头青丝无风自动,周身法力随心而起,一卷浩然正气化作的白练,撕裂空气,裹挟着她毕生的骄傲与愤怒,发出尖锐刺耳的呼啸,猛然抽向李冉那张让她感到无比恶心的脸。
“不知好歹的贱人!”
李冉眼中凶光大盛,反手一掌拍出。
尽管身受重伤,圣人位阶的威压依旧如山崩海啸般倾泻而出,雄浑的儒道圣力瞬间将她的攻击震散,磅礴的掌力余势不减,轰向她的胸口。
千钧一发之际,甄海瑶腰间玉佩骤然亮起,激发出一道濛濛青光,将那掌力层层化解。
但那毕竟是圣人一击,即便只是余波也非同小可。
甄海瑶却毫无顾忌,不闪不避,与李冉大打出手,灵力在华美的府邸中激荡碰撞,将无数珍贵的陈设化为齑粉。
然而,她的修为终究还是不及早已登临圣位的李冉。
若非他之前受的伤尚未痊愈,真气运转间依旧滞涩,实力大打折扣,甄海瑶恐怕早已在那一掌之下身受重创。
饶是如此,她也被震得气血翻涌,蹬蹬蹬连退数步。
但不知为何,李冉一掌击退她之后并未乘胜追击,而是猛地转头,朝甄府后院的某个方向望了一眼,眼神中满是忌惮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随后他冷哼一声,怨毒地瞪了甄海瑶一眼,整理了一下被劲气吹乱的衣冠,便一言不发地甩袖离去。
那一天的争斗,是他们两百年婚姻里的第一次。
那一战之后,恩断义绝。
甄海瑶以家主名义,不准李冉再踏入甄府半步,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此决裂,名存实亡。
一代儒圣,为求权位竟想献妻求荣。
如此下作不堪,令人作呕的行径,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等丑闻若是传出去,足以让整个儒林为之震动,让李冉苦心经营的圣人形象彻底崩塌,身败名裂,被天下读书人唾弃。
可她不能说,也不敢说。
甄家数百年的清誉,她父亲识人无数的名声,绝不能毁在她手里。
那份沉重到几乎要压垮她纤弱肩膀的家族责任感,她父亲临终前那双充满期许的眼睛,像一副无形的枷锁,死死地铐住了她想要玉石俱焚的冲动。
她只能打碎了牙,和着血,将这份蚀骨焚心的屈辱和愤恨咽进肚子里,独自一人,在无数个不眠的深夜里,反复咀嚼。
那段日子,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她如坠深井,井壁湿滑,寒潭刺骨,所有挣扎皆是徒劳,每一次抬头,所能望见的都只是那一方被井口框住的连星辰都吝于降临的死寂夜空。
她甚至一度想过,就此了结自己这荒唐可悲的一生。
而就在她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韩枭来了。
那个被她视作亲弟弟的少年,带着一身风尘,却依旧掩盖不了他身上那如同烈日般的阳光与锐气,再次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他是来寻李冉的,似乎有要事相商。
但当他从她那苍白的脸色和红肿的双眼中察觉到不对,再三追问之下,从她口中得知了李冉那禽兽不如的畜生行径之后——
少年那张总是带着几分懒散笑意的脸,第一次在她面前,阴沉得如同暴风雨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雷霆滚滚。
那双燃烧着火焰的星眸里,翻涌着她从未见过的滔天杀意。
他身上那股恐怖的凶煞戾气如同实质般弥漫开来,让她这个大修士都感到一阵心悸。
她也第一次这般真切地感受到了,【赤孽剑主】这令整个江湖都为之战栗的称号背后,究竟蕴藏着何等毁天灭地的凶威。
他毫不犹豫,没有半分迟疑,无比坚定地站在了她这一边。
他没有刨根问底,没有探究那些让她难堪的细节,只是安静地陪着她,用最真挚的关切与安慰,一点点温暖着她那颗几近破碎的心。
“没事了,海瑶姐,以后有我。”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能慰藉人心。
他用那双明亮得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她。
她在他眼中看到了愤怒与不平,那是为她而生的怒火。
然后,他张开双臂,给了她一个温暖而坚实的拥抱。
那一刻,井口的星辰纷纷坠落,一轮小太阳跃入井中,炸作粼粼光尘,将溺水之人从冰冷的深渊中,轻柔地捧起。
甄海瑶再也忍不住,她伏在少年那并不算宽阔却无比可靠的肩膀上失声痛哭,从压抑的呜咽到最后的嚎啕,将两百年的委屈、孤独、悲伤与绝望,尽数宣泄。
她从这个少年身上,体会到了久违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温情与庇护。
不是基于利益,不是基于名望,而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关怀与认同。
那是……真正的,可以托付一切的,家人的感觉。
……
自那以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也开始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一个她从未想象过的方向。
她知道,她的枭弟似乎在谋划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在一次深夜密谈中,他向她揭示了一个足以颠覆整个天下格局的宏大棋局。
他没有隐瞒,将自己的计划坦诚地展现在了她的面前,然后邀请她,成为这个棋局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成为他最信任的盟友。
看着枭弟向她伸出来的手,看着他眼中那份绝对的信任与期许,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手放进了他的掌心。
从那一刻起,她的命运,便与他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割。
她那颗死寂的心,因为他的存在,而重新开始跳动,并且每一次跳动都迸发出灼热且充满生命力的滚烫鲜血,冲刷着她身体里每一根干涸的血管。
自此,她成了他最坚实的后盾。
她毫无保留地动用甄家积累数百年的庞大财富,以及在儒门与朝堂中盘根错节的深厚影响力,为他铺路搭桥,为他扫清障碍,为他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情报与支持。
而他,也成了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精神寄托,成了她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他们开始更加频繁地见面,常常在深夜的书房里,借着微弱的烛光,一起探讨局势,推演未来。
她沉醉于他那与年龄不符的深沉谋略与无双胆识,更迷恋于他那身虽染杀伐却依旧不改初心的少年热血。
烛火跳跃,光影摇曳,将两人专注的身影拉长,投映在背后的书架上,交叠、融合,宛如一体。
那交缠的影子仿佛一个充满了情欲与宿命感的暧昧预言,每一次当她不经意瞥见时,那颗为他而复苏的心脏都会猛地漏跳一拍,随之而来的,是更剧烈更急促的擂鼓般的心跳,敲得她胸口发麻。
频繁的接触,如同文火慢炖,让两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愈发密切。
而那份原本纯粹的姐弟之情,也在一次次深夜的促膝长谈中,在一次次默契的相视一笑中,渐渐升温,变得越来越亲近,也越来越……微妙、色情。
因为在那文火之下,是她被压抑了两百年的欲望干柴,每一根都浸透了无尽的孤寂与渴望,正被这点点升温的暧昧烘烤得噼啪作响,随时都可能燃起燎原大火。
她开始贪恋,贪恋与他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次他离去后,书房里残留的他的气息,都能让她在空荡的房间里,痴痴地回味许久。
她甚至会悄悄坐回他刚刚坐过的椅子,用自己挺翘丰满的臀部去感受那尚未散尽的余温,将脸深深埋进他翻阅过的书卷里,像一个下流的变态,闭上眼睛,贪婪地大口嗅闻着那让她心安、心乱、甚至让双腿之间都微微发热的男人味道。
<如果……如果能就这样,和弟弟一直开心地生活下去,就好了。>
她不止一次,在夜深人静时,将自己赤裸的身体埋在柔软的锦被中,紧紧抱着那个还残留着他气息的软枕,把它夹在自己丰腴的大腿之间,感受着布料摩擦腿心最敏感嫩肉带来的羞耻感,像个无可救药的发情期痴女般,痴痴地想。
这个念头像一颗细小却拥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种子,一旦落下,便在她荒芜已久的心田中悄然生根,努力地汲取着每一次与他相处时带来的甜蜜与心动,作为最珍贵的养分,倔强地破土、发芽。
可人心总是贪婪的。
一旦品尝过甘泉的滋味,便再也无法忍受往日的干渴。
更何况,她品尝到的是能让枯骨生肉、死灰复燃的琼浆玉液。
所以当依赖变成了习惯,当欣赏演化为了倾慕,一些更加不切实际的念头便如同雨后的毒蘑菇,疯狂地从心田的土壤中滋生,争先恐后地冒出头来,每一株都带着令人晕眩的艳丽色彩与致命的诱惑。
不知何时起,她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属于女人的视角,去更加细致入微地关注,去重新审视这个被她一直称作弟弟的男人。
她会下意识地记住他爱喝的茶,爱吃的点心;她会在他来之前精心打扮,沐浴焚香,换上最能凸显自己丰乳肥臀曲线的紧身衣裙,那些衣裳是他曾无意中夸赞过的款式;她会因为他随意的一句关心而心如鹿撞,脸颊发烫,一整天都神思不属;她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最温柔端庄又暗藏风情的笑容,只为在他看向自己时,能展现出最美最勾人的一面。
她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追随着他的身影;她的心,会为他而牵动,他偶尔对自己的一个微笑就能让她欢喜雀跃一整天,在无人处偷偷回味,心满意足;她的情绪,会因为看到他对别的女子露出的亲昵眼神,而泛起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见的酸涩与嫉妒。
她看着他,又看着他身边环绕着的那些,或成熟丰腴,或明媚娇俏,或清冷绝艳,或英姿飒爽的绝色女子,她们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爱慕、崇拜与赤裸裸的占有……
那些眼神像一根根细小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她的心上,不致命,却带来绵延不绝的刺痛。
她开始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她们比较,比较容貌,比较身段,甚至比较谁的奶子更大,谁的屁股更翘,比较与他的亲近程度,但每一次比较的结果都让她感到一阵溺水般的恐慌。
那些鲜活的无所顾忌的女子,就像一朵朵盛开在阳光下的玫瑰,而自己,仿佛是一株只能在阴影中静静吐露芬芳的夜昙,纵有绝代风华,却见不得天日。
特别是看到那个叫雪儿的活泼少女与他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听到他对自己介绍雪儿是他的“小”娘子,这种恐慌直接到达了顶峰。
自己虽风华正茂,肉体熟得如同将要滴下蜜汁的果实,却毕竟年长他许多,还是个“人妻”,这让她在那个青春正盛的少女面前,感到一种无地自容的自惭形秽。
直到——
韩枭带着身份地位远远高于她的裴昭霁来到甄府暂居。